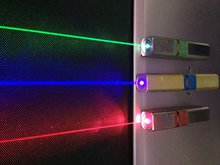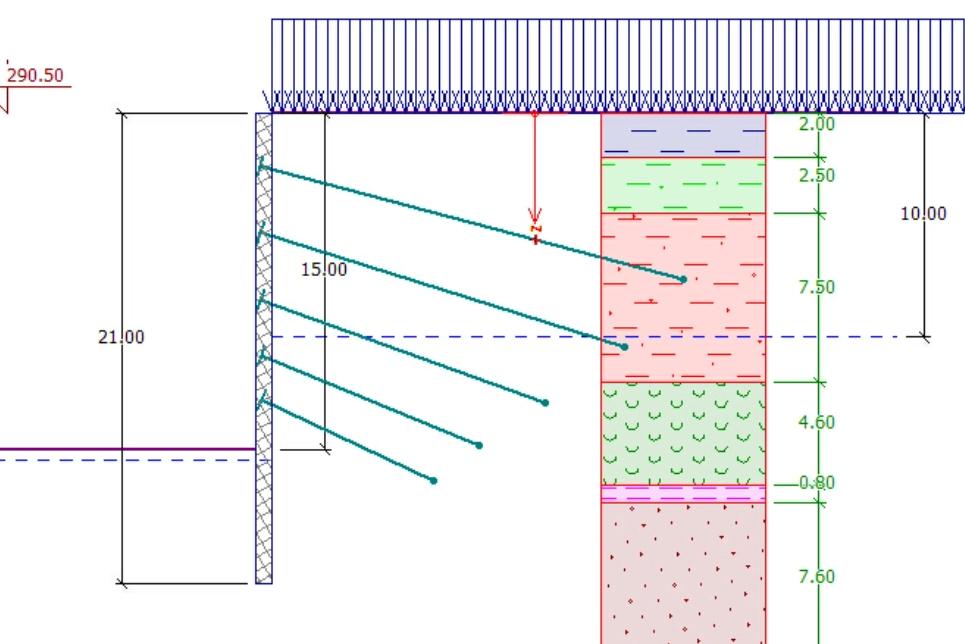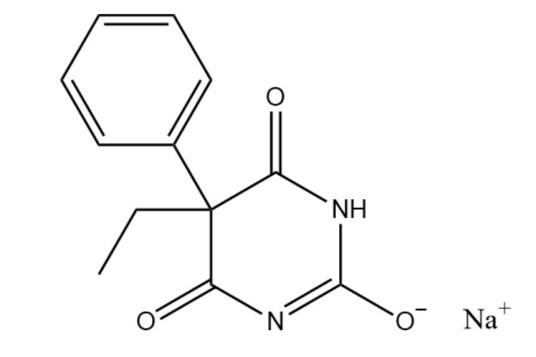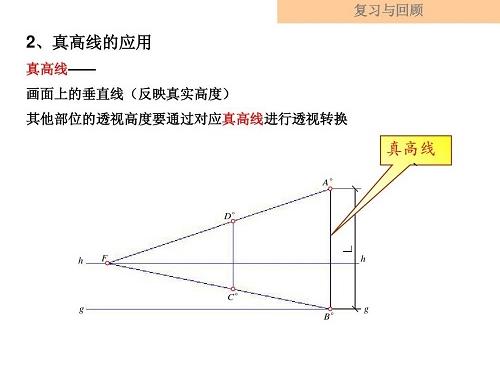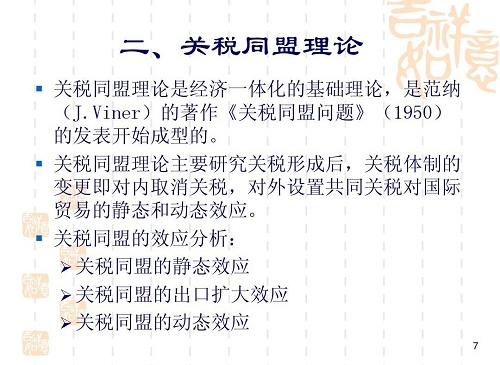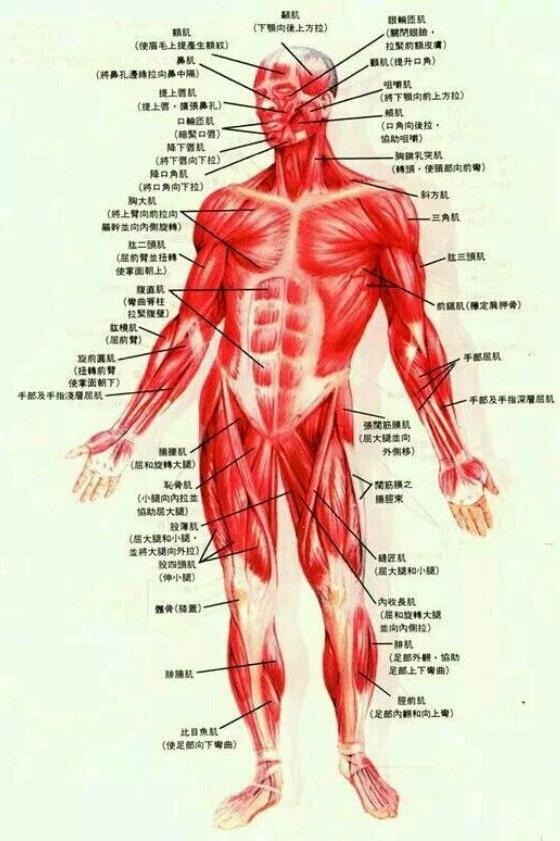概述
流浪漢小說--16世紀中葉,西班牙文壇上流行着一種獨特的小說。它的主人公大多是出身貧寒,有的是孤兒、私生子,童年、少年生活往往不幸,早年一般保持了天真可愛、富于同情心等品格。但當他們一旦脫離家庭、投入社會的懷抱,就感到無法适應,幹是為了活命、求得生存,不得不學着去阿谀、鑽營、撒謊、詐騙,他們中的不少人終于被社會同化,成為堕落者或狡詐無恥之徒。
作品通常在描寫他們不幸命運的同時,也寫他們為生活所迫而進行的欺騙、偷竊和各種惡作劇,表現了他們的消極反抗情緒。作品借主人公之口,抨擊時政,指陳流弊,言語竭盡嘲諷誇張之能事,使讀者在忍俊不禁之餘,慨歎世道的不平和人生的艱辛。
小說中的流浪漢都是動亂社會的特殊産物,他們是在不斷解決與周圍環境所産生的矛盾中觀察社會,認識社會,從而适應社會,求得個人的發展的;他們沒有什麼明确的道德标準來指導自己的行動,常常表現出玩世不恭的态度;在緊要關頭,他們往往見機行事,依靠自己的智謀求生存;他們總是以欺騙、偷竊等手段混日子或幹些惡作劇,以發洩私憤。
所以,這種文學體裁也稱為“消極抗議文學”。在題材上,它與中世紀的民間文學有相似之處,以描寫城市下層人民生活為中心,并且從城市下層人民的視角觀察與分析社會。它往往采取第一人稱,以自傳的形式描寫主人公的所見所聞,以人物流浪史的方式構建小說,用幽默的風格、簡潔流暢的語言廣泛反映當時人的生活風貌。它較為重視人物性格的刻畫,但主人公屬于性格通常沒有發展。比較典型的流浪漢小說——尤其是長篇一般都寫出主人公在社會上如何适應、也即由清變濁的過程。代表作--《小癞子》
小癞子
小癞子伺候一個又一個主人,親身領略人世間種種艱苦,在不容他生存的社會裡到處流浪,掙紮着生存下去,讓人體會出在窮乏低微的生活曆程中,癞子為求苟延殘喘所散發出不為勢屈的生命情調。《小癞子》,文字質樸簡潔,故事精采生動,真實反映中世紀西班牙的社會狀況,開啟流浪漢小說(Lanovelapicaresca)先例,并成為同類作品鼻祖。
曆史起源
16、17世紀在西班牙流行的以流浪者的生活及遭遇為題材的小說,它對西班牙和歐洲其他國家的文學都有一定的影響。
16世紀中葉,西班牙經濟開始衰落,人民群衆日益窮困,大批農民和手工業者破産,淪為無業遊民,商業經濟上升到比較重要的地位,社會上冒險的風氣盛行。流浪漢小說就是在這樣一種社會狀況下産生的。
最早的流浪漢小說《小癞子》,全名為《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刊于一五五四年,作者不明。小說以主人公小癞子的自述方式表達。他出身貧困,從小供人驅使,相繼給刻薄的瞎子領路,為吝啬的教士服役,替窮紳士行乞,最後靠不義之财,過着富裕的生活。在歐洲文學史上,一般将這部作品稱為流浪漢小說的代表作。
流浪漢小說的内容大多是主人公自述一生種種不幸的遭遇,借以反映當時嚴峻的社會現實,抨擊沒落中的貴族階級和教士,諷刺唯利是圖的資産階級觀念,使讀者在忍俊不禁之餘,慨歎世道的不平和人生的艱辛。小說中的流浪漢都笃信“天命”,以欺騙、偷竊等手段求生或進行惡作劇,以發洩私憤,不能進行積極的反抗,所以這種小說也被稱為“饑餓史詩”或“消極抗議的文學”。但其中有不少作品因大膽暴露貴族和教會的醜惡而遭到宗教裁判所的查禁和删改。
發展
流浪漢小說的一些特點,早在中世紀的某些作品如《真愛詩集》、《塞萊斯蒂娜》中即已有所映。它的代表作首推《托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1554,中譯本名《小癞子》),作者不明。
以後陸續出版的《古斯曼·德·阿爾法拉切的生平》(2卷,1599~1605),作者為馬特奧•阿萊曼(1547~1614);《流浪女胡斯蒂娜》(1605),作者為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烏維達;還有其他作品,在題材和手法上都相類似。
由于流浪漢小說受到歡迎,有些著名的作家也創作這種作品。克維多曾寫《流浪漢的榜樣,無賴們的借鑒,騙子堂巴勃羅斯的生平》(1603);塞萬提斯也寫了《林高奈特與戈爾達迪略》,收在《訓誡小說》中。17世紀下半葉以後,這種小說已經衰落,但在加爾多斯、阿拉爾孔、巴羅哈、帕拉西奧·巴爾德斯、巴列—因克蘭等人的作品中,仍出現流浪漢的形象。
特點
西班牙的流浪漢小說一般采用自傳體的形式,以主人公的流浪為線索,人物性格比較突出,主人公的生活經曆和廣闊的社會環境描寫交織在一起,已初具近代小說的規模。但是主人公的性格沒有發展,情節和情節之間缺乏有機的聯系。西班牙流浪漢小說對于以後歐洲小說的發展,特别在長篇小說的人物描寫和結構方法上,有過深遠的影響。
它反映了下層人民的生活,用下層人民的眼光去觀察和諷刺一些社會現象。主人公常是失業者,靠個人機智謀求生存,抵抗壓迫。他們沒有什麼道德标準來指導自己的行動,往往表現出玩世不恭的态度。這種小說和中古市民文學有相通之處。西班牙城市發達較晚,流浪漢小說就是城市發達後的産物。這種小說所反映的正是當時西班牙騎士傳奇作家所不屑于反映的生活,具有一定的現實主義成分。代表作品是《托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小癞子》)
社會影響
16世紀中葉,西班牙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道德日趨衰微,超塵絕俗的騎士文學和田園傳奇在當時的文壇上泛濫成災。在這種特定的曆史背景和文化氛圍中,流浪漢小說如異峰突起,它以一種嶄新的叙事結構形式,展現出五光十色的現實生活畫幅尤其是社會底層人物的喜怒哀樂,不僅在當時的作家和讀者心海裡刮起了一陣陣奇妙的文學旋風,而且給後世文學(特别是歐美文學)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從詞源上說,作為一個重要的文學術語,英語picaresquenovel(流浪漢小說)中的關鍵詞picaresque(流浪漢的)是從西班牙語picaresca移譯而來,他的西班牙語名詞形式是picaro,意即“違法者”、“無賴”或“惡棍”。由于西班牙流浪漢小說的影響,picaro這個詞很快被歐洲各國移譯成自己的語言,例如它的英譯通常是rogue、knave、sharper(流浪漢、惡棍、騙子),法語則譯為gueux、voleur(乞丐、竊賊),德語譯成Schelm、Abenteurer(淘氣鬼、冒險者),譯成意大利語則是pitocco、furbone(漂泊者、流浪漢),等等。
正是從picaro這個詞的基本含義出發,在外國學術界,有人将流浪漢小說稱為“騙子小說”。根據庫頓的定義,流浪漢小說是指“以流浪漢為主角的叙事作品。小說通過描述流浪漢的遭遇來諷刺當時的社會。”20世紀以降,由于流浪漢小說的基本特征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所體認,這一文學術語常常被用來指稱“第一人稱叙事體視角、插曲式結構、開放式結尾的描寫流浪漢遭遇的叙事作品”。
在中國,有人曾經将流浪漢小說稱為“惡棍小說”或“惡棍羅曼司”。而翻譯與研究流浪漢小說并且取得了卓越成就的楊绛先生則這樣界定:“按照一般文論的說法,流浪漢小說都是流浪漢自述的故事。流浪漢故事如果由第三人叙說,就不是流浪漢小說。自述的故事如果主角不是流浪漢,當然也不是流浪漢小說。”
此外,流浪漢小說的結構特征是“由一個主角來貫穿雜湊的情節”。這裡,楊绛先生要強調狹義上的流浪漢小說必須采用第一人稱叙事形式和插曲式結構,也必須采用一個真正的流浪漢作為小說的主人公。而“曆險性或奇遇性的小說盡管主角不是流浪漢,體裁也不是自述體,隻因為雜湊的情節由主角來統一,這類小說也泛稱為流浪漢小說。”
精神價值
在曆代歐美流浪漢小說中,出現了大量的流浪漢形象。歐美學者在研究流浪漢小說時,除了關注小說的叙事方式與結構特征之外,往往還要強調作品中必須有一個真正的流浪漢。
例如,美國著名的流浪漢文學研究專家紀昂就堅持這一觀點。那麼,什麼是真正的流浪漢呢?簡而言之,流浪漢最初是西班牙社會上廣大的破産者變成的無業遊民,他們出身微賤,從童年時代起就嘗盡饑寒交迫的苦味。流浪漢沒有固定家産和職業,到處受到欺騙和歧視,為了求得生存,隻好輪換地給一些主人當傭仆,同時也以狡詐的手段在社會上索取錢财。初出茅廬時,他們往往吃虧上當,後來逐漸學會在爾虞我詐的惡劣環境中欺騙他人。
他們對現實不滿而又無可奈何,想出人頭地而又玩世不恭。雖然偶爾也能發财緻富,甚至成為社會上的頭面人物,但他們不得不為此付出極大的精神代價。無窮無盡的流浪使他們到處都能看到社會的陰暗面,但他們并不想作出積極的反抗,而是采取了以惡抗惡的消極的生存方式。他們的命運浸染着濃重的悲劇色彩,腳下沒有一條能夠真正通向光明和幸福的路。
從藝術上看,一個典型的流浪漢其實是一個複合型的人物形象。
也就是說,那些頻繁出現在歐美不同時代不同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如一個小醜、一個流浪詩人、一個無賴、一個土匪、一個浪子、一個小偷、一個暴徒、一個攔路強盜、一個乞丐、一個漂泊者,或者像莎士比亞筆下福斯塔夫式的一個撒謊者、一個吹牛大王、一個好心人、一個懦夫、一個機智的人、一個僞君子、一個道德哲學家、一個喜歡誇張的雄辯家,加上紀昂所說的文藝複興時代流浪漢的三大先驅——漫遊者、窮人與騙子……
都為最初或後來的流浪漢形象提供了藝術原料。也就是說,一個典型的流浪漢形象,往往融合着上述各種人物形象的藝術基因。
流浪漢是多少帶有一些喜劇色彩的悲劇人物形象。他的喜劇性表現在行為方面,而他的悲劇性則表現在命運方面。流浪漢的言語行動常常是機智幽默的,富有喜劇色彩,但在追求理想生活的過程中,由于出身寒微、地位卑賤、力量薄弱,加上他常常采取以惡抗惡的生存方式,所以他忍受了許多屈辱,經曆了許多失敗。
有的流浪漢偶爾或最後在物質生活方面獲得了一點勝利,但隻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就會發現,那不過是暫時的甚至是虛妄的勝利。小癞子最後依傍聖瓦爾铎的大神父解決了溫飽問題,而且娶了大神父的女傭為妻,但大家都知道他背負着難以啟齒的屈辱(大神父與女傭長期私通),付出了慘重的精神代價;吉爾·布拉斯依靠自己的機智與才幹,曾經獲得了高位與财富,但他卻逐步滑向了堕落的泥淖,到頭來還是失去了一切。
不過,在整個流浪過程中,流浪漢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和他的堅持不懈的行動,猶如希臘神話中西西弗斯的巨石,帶給讀者的是極大的美學價值與精神價值。
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與文學家加缪在他的哲學随筆《西西弗斯神話》裡,對西西弗斯的絕望處境與奮鬥精神作出了富有哲理的描述。他同情西西弗斯的不幸命運,更欣賞西西弗斯的精神品格:“我看到這個人下山,朝着他不知盡頭的痛苦,腳步沉重而均勻。”“造成他的痛苦的明智同時也造就了他的勝利。”
他敢于正視那塊巨石,敢于把一次次滾下山的巨石再一次次推上山頂,這決不是表明了他的無奈與愚笨,而是表明了他對不幸命運的蔑視與反抗,同時也是對一種荒誕的生存狀态的蔑視與反抗。所以,加缪說道:“征服頂峰的鬥争本身,足以充實人的心靈,應該設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不過,這種幸福是一個冷漠的人在冷漠的世界體驗到的幸福,等同于加缪的小說《局外人》的主人公莫爾索在臨刑前夜以發洩滿腔怒火的方式向神甫表達的幸福感受:“現在面對着這個充滿了星光與默示的夜,第一次向這個冷漠的世界敞開了我的心扉。我體驗到這個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愛融洽,覺得自己過去曾經是幸福的,現在仍然是幸福的。”的确,流浪漢、局外人、西西弗斯在行為方式、命運際遇和精神品格等方面存在着許多相似之處,他們的生活構成了一種“西西弗斯節奏”。
也許正因為看到了流浪漢、局外人、西西弗斯之間的精神聯系,美國學者劉易斯(R.W.B.Lewis)才在他的學術專著《流浪漢的聖徒:當代小說中的典型人物》中,對加缪的哲學随筆《西西弗斯神話》、小說《局外人》以及美國當代小說中的流浪漢形象先後進行了濃墨重彩的論述。
在歐美學術界,的确有許多學者都對流浪漢形象進行過比較深入的研究,其中有的學者提出了精辟的見解,也有一些學者對流浪漢形象的認識是片面、偏頗乃至錯誤的。
就連紀昂這樣的流浪漢文學研究大家的觀點,常常也是有正有誤,有瑜有瑕。例如他指出:“因為流浪漢是一個批評家和一個反叛者,所以他的叛逆态度包含着積極的精神價值。……他的格言,正如考狄納斯所強調的那樣,主要是古代犬儒學派門徒的格言:自給自足和獨立自主就是幸福狀态,為此必須犧牲物質享受、财富、榮譽、地位和愛情。就像流浪漢一樣,犬儒學派的門徒對家庭或家鄉漠不關心,喜歡采取一種禁欲主義的生存方式。他像反對崇拜偶像并且熱衷于現在的無賴一樣,依靠經驗主義解決自己的生活,從不信奉真理。”
在這裡,紀昂把流浪漢和古代犬儒學派門徒相提并論,說“流浪漢是一個批評家和一個反叛者,所以他的叛逆态度包含着積極的精神價值”,說流浪漢覺得“自給自足和獨立自主就是幸福狀态”,并且“依靠經驗主義解決自己的生活,從不信奉真理”,這些見解都是中肯的。
然而,紀昂斷言流浪漢像犬儒學派的門徒一樣,為了自己的信仰“必須犧牲物質享受、财富、榮譽、地位和愛情”,甚至“喜歡采取一種禁欲主義的生存方式”,這樣的觀點就有失公允,不符合絕大多數流浪漢小說中的實際描寫。好在紀昂緊接着又作了這樣的補充:“但流浪漢并未堅定不移地遵守這一古代的道德格言。假如他遵守了,那麼他的生活就會更加單純。從這個意義上講,我不能完全同意考狄納斯的看法,他認為田園傳奇的主人公和流浪漢小說的主人公同樣體現了對邪惡社會的反抗,同樣強調了回歸自然——16世紀人文主義者的自然主義。
依這位批評家之見,流浪漢本該是社會中的自然人,隻是被他感到毫無關系的社會群體所束縛。但流浪漢和牧羊人的基本生活水平卻是截然不同的。……他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受到迫在眉睫的饑餓的折磨。盡管他後來喜歡表現出哲學家的言談舉止,但他卻不得不設法解決眼前的溫飽問題……由于這個緣故,流浪漢的行為是自相矛盾的。通過人物反抗社會價值而又追求同樣的價值之間搖擺不定的舉動,流浪漢小說表達了主人公的這種困境。古代犬儒學派的哲學主要是消極的,除了自由與平靜之外,差不多所有的世俗價值都受到流浪漢哲學家的蔑視。”
值得注意且饒有趣味的是,關于流浪漢那種複合型的人格要素,關于流浪漢行為與命運的“西西弗斯節奏”,關于流浪漢那種令人哀傷的“幸福”感及其“局外人”身份,在米勒、威克斯和紀昂等學者的著作中,同樣可以看到上述的一些觀點。英國學者蒂莫西·G·康普頓把米勒、威克斯和紀昂等人的見解綜合在一起,總結出流浪漢形象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一個單純的主人公。紀昂指出:“每一部不折不扣的反映流浪漢生活的小說,都可以用一個單純的名字來描述。”對于一部堪稱真正流浪漢體的作品來說,一個單純的反英雄的主人公的存在絕對是不可缺少的。
(2)不同尋常的出身。“圍繞着流浪漢進入大千世界的環境往往是不同尋常的,因此這些環境成為各種各樣的征兆。”有些流浪漢出身于底層社會,他們從不了解母親的身份,對父親的身份更是缺乏認識。無論從字面意義上還是從比喻意義上來說,流浪漢差不多總是一個孤兒。他享受不到親情,所以流浪漢一出生就發現自己陷入了一種雜亂無章和動蕩不安的生活狀态。
(3)狡猾。流浪漢是“一個愛管閑事、蠻橫無理、富有彈性、孤苦無依的人物形象,他苦心經營,不過是為了在其雜亂無章的生活場景裡苟延殘喘,但在人生的枯榮沉浮中,他也能對大千世界采取強有力的防守姿态。”紀昂指出,流浪漢“并非都惡棍化了——騙子總是盡可能依靠他的機智生活,他的狡猾真的算不上什麼罪過。詭計與欺騙隻是他進攻的武器,而保持一種淡泊的快樂心情,這又是他防禦的武器。”不管處境多麼艱難,流浪漢總得千方百計地活下去。
(4)千變萬化的形态。最典型的流浪漢總是扮演若幹不同的角色。他能給一系列主人當傭仆,或者頭戴大量職業面具,身穿大量職業服裝。“沒有流浪漢不會扮演的角色。”就其适應性來講,流浪漢的個性曆來都不好清晰地界定。從悖論上說,在流浪漢逐步變成“平常人”的過程中,他又變成了非人。
(5)疏遠。紀昂把流浪漢稱之為“半個局外人”。盡管他總是涉足社會,但他從未完全融入社會。在他的生活中,愛與忠誠的缺失導緻他跟人和事割裂開來,他變成了米勒的所謂“漂泊不定的一半”。有時,流浪漢似乎快要融入社會了,但西西弗斯節奏又占了上風,于是他發現自己和社會更加疏遠了。
(6)内心動蕩不安。正因為流浪漢的混沌的出身、千變萬化的形态及其和社會的疏遠,這就自然而然地導緻了他内心的動蕩不安。他不能執行自己的決策。也就是說,一時的沖動、好奇心和惡作劇支配着他,使得他遇事不能打定主意,作出決策。(7)哲理傾向。這一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來源于(小說的)叙事立場,同時也來源于流浪漢的好奇心和善于觀察的機敏天性。因為流浪漢講述的是發生後的故事,所以他動不動就用一種哲學的方式對那些經曆評頭論足。他對社會、政治與人性的洞幽燭微的感想,表明了一種積極而又周到的智慧。
中國狀況
吳培顯在《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4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國的“流浪漢小說”随着20世紀90年代的社會轉型而興盛。與西方流浪漢小說相比,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作家雖然同樣是在關注和反映城市流浪漢的生存或漂泊狀态,但作家們并非僅僅停留于“從下層人物的視角去觀察、諷刺不合理的社會現實”的層面,也不滿足于表現流浪漢們“由清變濁的過程”等,而是在各自不同結構的城市流浪叙事中,敏感捕捉并廣角鏡般地攝取市場化轉型期光怪陸離的城市欲望,傾情關注這些深處都市生活下層、漂泊于城市欲海之中的流浪漢們複雜的人生軌迹和心路曆程,揭示他們深層的精神世界及其個性化的人生取向和價值追求。
都市尋夢者的心路曆程是以自我價值的積極追尋為起點,經由欲海漂泊的窘迫和迷茫,以價值理想的扭曲及其悲劇結局而告終;“剩餘勞動力”是在自我被動否定的起點上,經由觀念的内在沖突和人生的曲折追求,達到戲劇性的自我價值确證的人生目标;身心無根漂浮的都市下層“玩家”的人生軌迹,則是以否定性的社會角色為起點,經由物質生存的奮争,終因價值目标的先天性局限而再度跌到否定性的人生起點上。由此反映出作家對都市流浪漢的價值定位的差異。
在中國,流浪漢小說并沒有被過多提及,其實中國的許多著名作家的小說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經可以劃分到流浪漢小說的範疇中。
首先是錢鐘書的《圍城》,整體采用流浪漢小說的框架,其次,餘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也可以算是流浪漢小說的雛形。另外一個可以算是中國流浪漢小說集大成者,張炜。
張炜所創作的小說中,“流浪漢”形象的反複出現,以及其深層中對“流浪情結”的“情有獨鐘”,使得他的小說與西方傳統的“流浪漢小說”有了不謀而合的相似之處。
這種相似主要表現在:一、都有一個“流浪漢小說”的框架;二、都有着相似的小說整體的叙事方式;三、都有着基本相似的創作背景;四、各自小說自身的變化脈絡也有着暗合——即都由對單純的現實生活的流浪的描寫發展到後來的對因生活驟變導緻的思想無着的生活和精神的雙重流浪的描寫。相似中也有相異,張炜創作“流浪漢小說”的非自覺性,以及他的小說中反映出來的獨有的宗教情愫都是他與傳統的流浪漢小說不同的地方。
在閱讀張炜的小說時,另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引起人們的注意。那就是張炜的小說中反複出現了很多“流浪漢”的形象,例如:《遠行之囑》中的“我”,要告别姐姐遠行,要去流浪;《秋天的思索》中的李芒,從家鄉流浪到南山,又到東北;《遠河遠山》中的“我”也是一個小小的流浪漢,為了尋找一個個“文學老師”,“我”一個人走出了家門,走向了大山;《你在高原》和《懷念與追憶》中的甯伽,還有老莊,他“是一個真正的流浪漢......”
《古船》中的隋不召帶着《海道針神》寶書出海了;《柏慧》中的“我”,為了探求一個家族真相,也在尋找中苦苦流浪;《家族》中的許予明,也是一個不安分的流浪者的形象,它是一個革命者,但卻壓抑不住心中無法述說的流浪欲望;《外省書》中的師麟——“鲈魚”,一直在奔跑流浪,他的流浪幾乎是一種不安分的本能,既使屢次受到來自個方面的懲罰,仍停不下流浪的腳步;《醜行或浪漫》中的劉蜜蠟。
為了尋找自己“精神上的引路人和知識的啟蒙者”——雷丁老師和“真性愛人”——有着古銅色皮膚的俊美少年銅娃,從“下村”的“大河馬”家一路奔跑,向南,向北,沿着蘆清河,從鄉村流浪到城市,二十年多年沒有停下腳步。劉蜜蠟“是一個奔跑的女神”。《九月寓言》中的小村人一直在“奔跑”,那是一個奔跑的世界,裡面有無數個奔跑的形象。在《九月寓言》中特意被告知,小村的形成始于滿世界奔跑的流浪漢們決定不再盲目闖蕩,不約而同地說“停吧,停吧”!
“我們面對的不僅僅是一個熟知的世界,還有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我感覺有好多事情要去做,好多路要去走。”“我跟随的是無影無形的一條小路,它沒有盡頭,......但我望得見它,即使眯上雙眼也會準确無誤地跟定。像被一股奇特的力量所牽引,我的雙腿輕捷暢快,背上的行囊也不似從前那樣沉重。
沒有饑餓的折磨,沒有困倦的侵擾,說不清走了多久多遠......我傾聽着藏在心底的呼叫......我在喊:天哪,等等我,我來了......”“我在山區和平原、在野地裡奔來奔去。一種渾然蒼茫的感覺籠罩了我。難以言喻的蓬勃生氣、它的獨特力量,長久地給我以支持。我認為自己的血液中流動了、保存了它的特質,我現在要做的隻是與大地進一步相接相連,讓血液中固有的東西變得更濃稠、加快旋動。這樣才有可能催生出新嫩的鮮活,從而使陳舊的盡快蛻去。
在這個過程中,人會一再地感激領悟到那份真實和永恒,極為厭棄那些虛僞的泡沫,輕視那些過眼雲煙......”“人需要一個遙遠的光點,像渺渺星鬥。我走向它,節衣縮食,收心斂性。願冥冥中的手為我開啟智門。比起我的目标,我追趕的修行,我顯得多麼卑微。蒼白無力,瑣屑庸懶,經不住内省。就為了精神上的成長,讓誠實和樸素、讓那份好德行,永遠也不要離我,讓勇敢和正義變得愈加具體和清晰。那樣,漫長的消磨和無聲的侵蝕我也能夠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