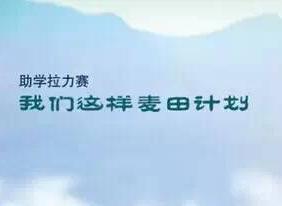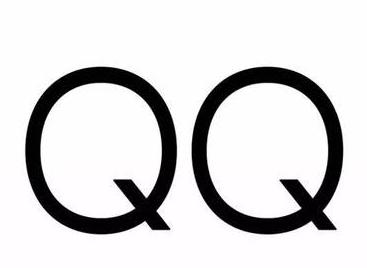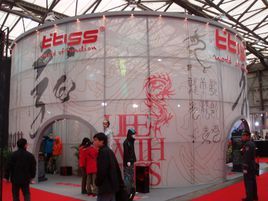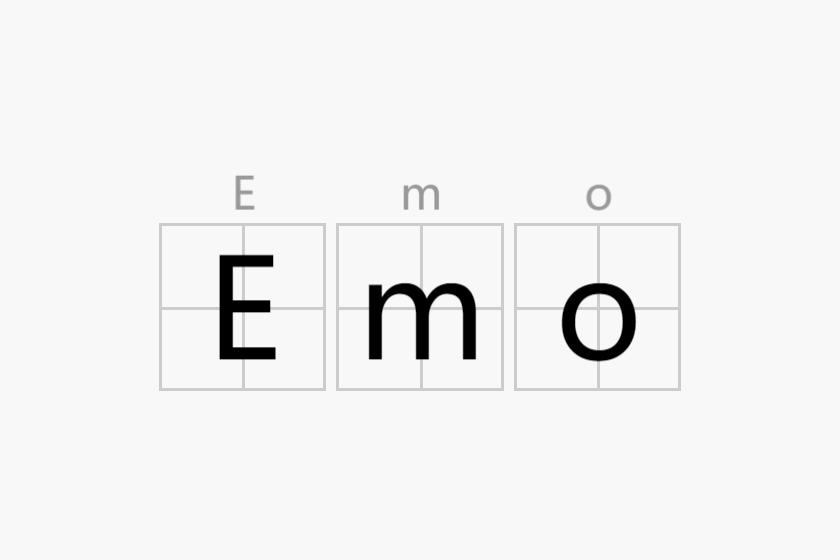定義
死亡賠償金是指被侵權人因侵權人的侵權行為而死亡,侵權人應當支付給被侵權人近親屬的金錢賠償。
法律規定
民法典的規定
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條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損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營養費、住院夥食補助費等為治療和康複支出的合理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造成殘疾的,還應當賠償輔助器具費和殘疾賠償金;造成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和死亡賠償金。
第一千一百八十條
因同一侵權行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數額确定死亡賠償金。
法律意義
死亡賠償金的意義在于維持近親屬與被侵權人死亡前大緻相當的物質生活水平。死亡賠償,是财産性質的損害賠償而非精神損害賠償;是對近親屬自身利益受損進行的救濟,而不是對生命本身的賠償,所以不存在“同命同價”或者“同命不同價”的問題;是近親屬自身依法享有的損害賠償請求權,而不是從死者處繼承來的損害賠償請求權(《民法典》第1181條第1款)
四、常見問題
死亡賠償金的計算
死亡賠償金的計算,主要考慮死者的年齡、當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或者人均純收人、被侵權人死亡前的收人等因素。《民法典》第1 180條規定:因同一侵權行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數額确定死亡賠償金。
案例分析
何青某等訴劉定某等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
——死亡賠償金的性質探析
案件詳情
2005年12月15日淩晨6時許,重慶市某區某街道租房居住的何青某夫婦到農貿市場賣豬肉,其女何源與兩同學乘同一輛三輪車,結伴去學校上學。當三輪車行駛到某長城公司上坡路段時,迎面駛來的一輛滿載貨物的卡車(渝B28355)刹車不及,車輛失控,發生側翻,壓住三輪車,緻車上三學生當場死亡。
經查,渝B28355号卡車登記車主為重慶鋪金公路運輸有限公司,實際車主為劉豐某,肇事駕駛員劉定某(已判刑三年)。2006年1月7日,交警認定劉定某負事故全部責任。
事故發生後,各方當事人自願選擇協商解決方式。在有當地政府、交警等參與下,2005年12月17日,各方當事人達成賠償協議,兩位城鎮戶口女孩的家人各自得到了20餘萬元的賠償。14歲的何源雖然從出生時起就随父母在屬于重慶主城區的某街道生活,但因是農村戶口,按當時的法律規定,何青某夫婦隻得到5萬餘元的死亡賠償金和4萬元的補償金。
僅因戶口上的城鄉差異,就使同一車禍中受害人死亡損害賠償額出現天壤之别,一時間,該判決結果及判決依據旋即在全社會引起了軒然大波,而對于“同命不同價”的批評更是鋪天蓋地。的确,同樣是生命,為什麼在賠償上會有如此巨大的差别,怎樣賠償才算是公平的,其賠償的标準為何,我們又将如何讓看待現行的死亡賠償金制度呢?無疑,這些問題能否得到回答,不僅直接關系到死者及其近親屬的切身利益,而且,它也必定會影響到法院權威的樹立,甚至,對于社會的穩定和政局的安定都會有或多或少的影響。
法律評析
一、對“同命不同價”的反思
通過分析,可以看出上述案件的最大争議就是:同樣是生命,為何卻因戶口上的城鄉差别造成了“同命不同價”?的确,法院為何會做出這樣的判決呢?這種結果的發生,是由于司法判決中出現了徇私舞弊的現象,抑或,我們的立法層面出了問題?以下,筆者将依次展開論述。
1、考量判決的合法性
通過上文對案件的介紹,我們可以明确地對案件做出一個定性:本案是一起侵犯生命權的案件,肇事駕駛員劉定某侵害了何源等三名同學的生命權,他們之間是侵權法律關系,因而該案件最終适用的法律也必須是有關侵權責任的法律規定。反觀法院判決,本案的法院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2003年12月4日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适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二十九條,即“死亡賠償金賠償标準為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
應該說,排除其它的可能性,僅就判決的理由和過程而言,“同命不同價”的判決結果是在情理之中的。換句話說,依照現行法律的相關規定,“同命”就應該“不同價”。這樣的分析結果多少讓人有些意外——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它甚至比法官在判決過程中徇私舞弊更使人恐怖,畢竟法官的徇私舞弊隻是污染了水流,而制度本身存在問題則是污染了水源。行文至此,問題就轉向了:現行制度為何會做出這樣的規定,它是怎樣産生的,又是基于怎樣的考慮?
2、《解釋》及其出台背景
應當說,在《解釋》之前,相關的法律法規已有對死亡賠償金的規定,例如:《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造成死亡的,應當支付喪葬費、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産品質量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因産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應當支付喪葬費、撫恤費、死者生前撫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四十二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造成消費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的,應當支付喪葬費、死亡賠償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養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費等費用;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并且《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1991年)的第37條第8項的規定,在“被扶養人生活費”以外,又規定了“死亡補償費:按照交通事故發生地平均生活費計算,補償十年。對不滿十六周歲的,年齡每小一歲減少一年;對七十周歲以上的,年齡每增加一歲減少一年,最低均不少于五年。”
可以說,在以上幾項法律法規中,尤其是後兩項法律中,已經明确提出了:在“喪葬費”和“被扶養人生活費”以外,同時給付“死亡賠償金”或者“死亡補償費”——盡管與死亡賠償金說法不同,但是它們并沒有對死亡賠償金的性質作出明确而細緻的界定。由于法律對死亡賠償金性質的模糊規定,以至于在審判實踐中,對于這一問題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認識。一種認識是:死亡賠償金既包括物質性損害賠償又包括精神損害賠償,如自2001年3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确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幹問題的解釋》第九條規定:“精神損害撫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緻人殘疾的,為殘疾賠償金;(二)緻人死亡的,為死亡賠償金;(三)其他損害情形的精神撫慰金。”顯然,死亡賠償金在此處被界定為精神撫慰金。另一種認識是:死亡賠償金僅限于物質性賠償,如法釋(2002)17号《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問題的批複》對附帶民事訴訟和獨立民事訴訟的法律适用作了限制性區分,規定:“對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精神損失提起的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在該刑事案件審結以後,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也就是說,在犯罪引起的導緻受害人死亡的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對受害人的賠償僅限于物質性賠償。
兩種不同的立法定位,使死亡賠償制度在司法界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這不僅不利于法制的統一,更危險的是,法律的不确定性使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了嚴重的損害。有鑒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借鑒我國司法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參考世界各國成熟作法,于2003年12月4日通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适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第二十九條将死亡賠償金定位于物質性損害賠償,且統一了賠償原則和标準。
3、《解釋》的意義及現實難題
總的來說,該解釋的出台為受害人及其親屬提起死亡損害賠償提供了法律依據,擴大了為死亡賠償金的适用範圍提供了一個明确的标準,解決了以前立法上的存在沖突問題,同時,它也體現了對人的價值和權利的尊重。事實上,《解釋》出台伊始,學術界對其評價極高,很多學者認為“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的最重要意義,就在于确認和凸現人的價值、人的法律地位和權利本位思想……突出人的價值、突出人的地位,就是要更好地保護這些權利,救濟這些權利的損害,以保護人的價值、維護人的尊嚴和地位。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立足于這一立場,凸現民事司法的人文主義立場,全面保護人的權利,救濟人的生命權、健康權和身體權的損害,體現了民法的人文主義關懷,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精神損害賠償的司法解釋一道,成為新中國人格權司法保護中的最重要的兩個司法文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客觀地講,該解釋在我國民法尤其是在侵權行為法的建設中,在保護人的權利方面,的确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然而,為何這項被學界評價極高的解釋,在近些年的司法實踐中卻越來越遭到人們的廣泛質疑呢?要探求問題的根源,我們有必要對這項解釋有更深入的了解。通過分析《解釋》全文,可以明确上述問題的症結其實在于第二十九條是否合理,即:以死者的城鄉居民身份的差異而适用不同的賠償标準是否合适。
結合民衆對“同命不同價”的聲讨及《解釋》第二十九條的規定,有相當多的人認為,造成“同命不同價”這種差異和歧視的根源就在于我國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結構,在改革開放迅猛發展的今天,這項制度越來越不合時宜。因而,現階段隻有取消戶籍制度并改革潛藏在戶籍背後的勞動、人事、教育、财政、金融、福利、司法等制度才能真正達到“同命同價”。然而,也有學者指出:“死亡賠償的城鄉差異僅僅是我國近年來所遇到的一系列死亡賠償案件的典型,若過度聚焦于此,不利于多角度、全方位地把握死亡損害賠償的法理,無助于搭建叩問‘同命同價’的理論平台。”
因此,我們認為,要解決“同命不同價”的現實難題,有個前提問題就必須明确,即:死亡賠償金的性質究竟為何?隻有在明确這個前提下,我們才能以此确定相應的賠償标準或賠償數額。以下,本文就将對死亡賠償金的性質展開分析。
死亡賠償金性質探析
1、屬性上,補償性抑或懲罰性
筆者認為,死亡賠償金應兼具補償性和懲罰性兩種因素。主要理由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生命權作為最重要的人身權,當死者本人非自願的被剝奪了這最寶貴的權利時,死者本人遭受的是最大的傷害。如果僅僅因為受害人無法主張任何權利,就此認為死亡賠償金不是賠給死者的,是對生命權的極大不尊重”。同時,對于加害者來說,其負有不侵犯他人合法權利的義務,死者的生命權受到最大程度的侵犯,也是侵權者最大程度的違反義務,因而,“從這個角度,死亡賠償金還具有對侵權者的懲罰性質。”
當然,加害人侵犯公民生命權後,究竟會産生什麼樣的請求權,也就是說雖然死亡賠償金具有補償性是無疑的,但是權利主體卻并不一定唯一。
2、對象上,安撫生者抑或補償死者
筆者認為,死亡賠償金亦兼具安撫生者和補償死者兩種因素。具體而言,死亡賠償金基于公民的“生命權”受到損害而産生,但是在客觀上表現為既侵害了公民的“生命”,又給公民的親屬造成了心靈創傷。本來,按一般民事理論,主體不存在,相應權利也應消亡,但是畢竟生命權具有特殊性,正如前文所說的,“雖然在很多學者看來,任何試圖以貨币的方式對人的生命進行定價都是對人格尊嚴的一種貶低。但是在很多時候,無價的生命往往要通過一定的方式進行定價才能得以維護相關當事人的利益。”因而,為了體現對死者生命權的尊重,需要也應該用一定數額的金錢或者其他物品,來表現死者生命的價值與意義。這既是道德上對于死者的尊重,同時也是法律保護公民“人身權(人格權)”的應有之意。同時,由于公民的死亡,也不可避免地給其親屬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因而,依據侵權法的相關規定,要求加害人予以賠償也自然順理成章。
在這裡,需要強調的是,無論是對死者的補償還是對生者的安撫,都是基于公民的生命權受到損害這一法律事實産生。而由于公民已經死亡,我們不可能讓加害人把象征公民生存價值的這部分賠償金丢在死者的屍體上或讓加害人僅僅口頭上宣布賠“它(此時死者已是屍體,是特殊的物)”多少,而應該讓加害人将賠償金交給特定的民事主體。這類民事主體就是而且隻能是死者的近親屬,而不能是死者的朋友、同學、老師甚至其他人。理由很簡單,依照我國婚姻法的規定,夫妻雙方一方死亡,婚姻關系當然終止。也就是說,在一方死亡後,對于另外一方來說,死者不再是“丈夫”或者“妻子”,而是——盡管筆者很不願意這樣說——和他(她)不再有任何法律關系的一個物,隻是由于該物的特殊性,另外一方對其隻負有妥善保管及時安葬的義務,而無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既然如此,死者生前的财産理應與另一方無關,但是,在繼承法上,卻又明确規定另一方具有繼承的權利。可以看出,我國法律是通過技術拟制的方式來作出理論上的解釋,即:既承認公民死亡後,與之有關的人身關系當然消滅,又在一定程度上允許基于人身關系産生的财産關系繼續存在。這也是筆者認為對死者的賠償金需要交給其近親屬的原因所在。
3、内容上,财産賠償抑或精神撫慰
在這一問題上,我們認為,死亡賠償金是一種精神賠償,但是,在具體賠償時,應将對死者和生者(其近親屬)的精神損失加以“分割賠償”。提出上述主張的理由在于:一,對于死者而言,如前所述,生命權受到損害本身無法彌補,對其進行賠付是為了體現對死者生命權的尊重,那麼,既然是尊重,那麼這種賠償金就隻能是精神損害賠償或者說“類似于精神損害的賠償”。二,對于死者家屬來說,該公民的死亡無疑在精神上給其家屬帶來了巨大的傷害,要求精神損害賠償理所當然。但是,需要說明的是,在客觀上,雖然,公民的死亡間接地斷絕了死者親屬的撫養費用,并且在正常的餘命年限中可以留給其繼承人的财産不能兌現,但是,“對該部分賠償(補償)”既無法律上的依據,也無法在邏輯上得出這種結論。因此,筆者認為,對死者家屬的賠償隻能限于精神損害賠償。
結論
在當今中國,随着一個又一個有關死亡賠償案件的出現,同命不同價的批評鋪天蓋地,我們急需對這一問題産生的原因以及背後所隐含的實質進行研究。事實上,在這一點上,我們的學者也進行了長時間的不懈努力,提出了一些較為“公平合理”的解決方式,但是,由于囿于國外的學術主張,雖然衆說紛纭,但均未明确死亡賠償金的性質這一問題的核心。所以,即使我們将死亡賠償金的内容和标準設計的多麼周全,到頭來都隻能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都無法回答“同命不同價”是如何産生的,“同命不同價”是否真的不合理,賠償的是死者的命還是其他等等問題。尤其是,當大多數人将“同命不同價”的矛頭指向戶籍的差異,進而指向中國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結構時,事實上,我們已經在死亡賠償金的性質問題上越走越遠。
在本文中,筆者以重慶發生的一起三輪車緻人死亡案件出發,通過對案件判決的合法性以及所适用法律的正當性考量,指出産生“同命不同價”批評的根源在于沒有認清死亡賠償金的實質,進而筆者通過對生命權特殊性的研究以及國内外各種關于死亡賠償金性質的觀點,認為死亡賠償金基于且僅基于公民生命權受到損害而産生,并在此基礎上明确了三個問題:一,就屬性而言,死亡賠償金既具有補償性又具有懲罰性;二,就賠付對象而言,死亡賠償金既是對生者的安撫又是對死者的補償;三,就内容而言,死亡賠償金僅僅是精神性賠償,隻不過對生者和死者的賠付标準有所不同。應該說,筆者的上述主張既體現了對生命權的尊重,又兼顧了死者近親屬的利益,最重要的是,上述主張解決了“固有侵害說”和“繼受說”的根本缺陷:公民死亡就必須對其近親屬進行賠償的合法性(正當性)問題。
當然,由于我國立法中對死亡賠償金性質的認定采納的是“繼承喪失說”的觀點,以至于無論以此确定的死亡賠償金的賠付内容和賠付标準為何,都必然導緻“同命不同價”的發生。應該說,本文對死亡賠償金的性質已經為死亡賠償金制度的完善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但是筆者也清醒地認識到,有關死亡賠償金的具體賠付标準及賠付内容的确定還需要考慮諸多方面的因素,故應在此基礎上進行更深入和細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