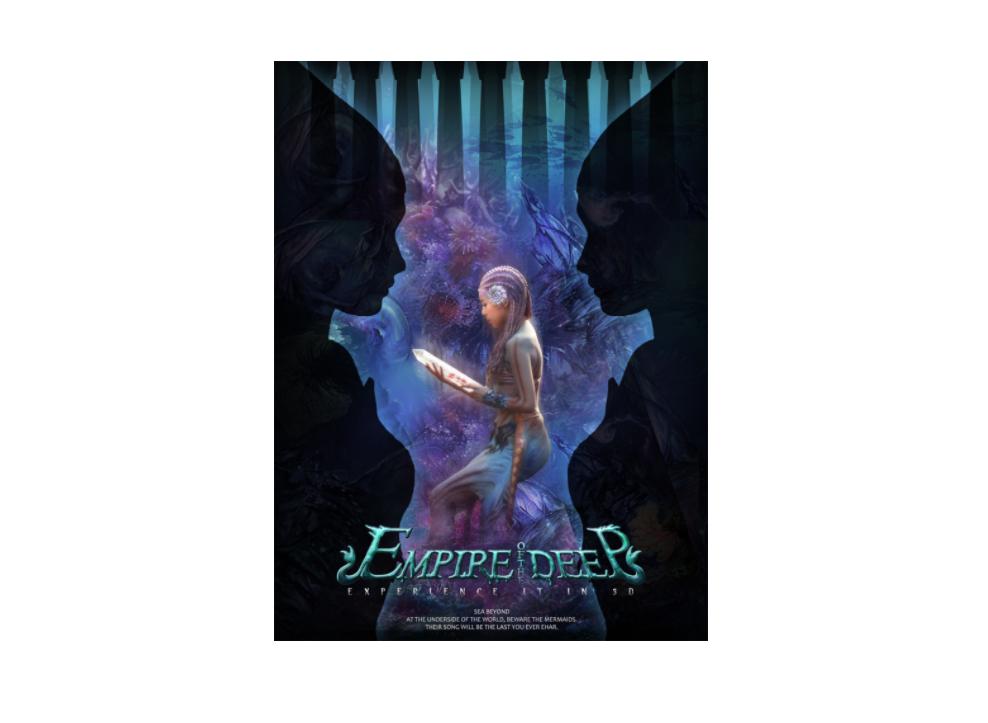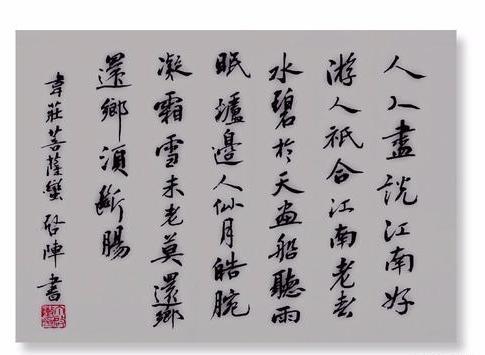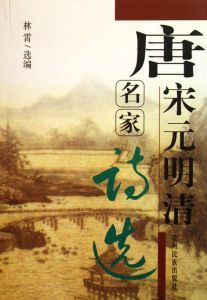作者小傳
韓非(約公元前280-前233年),出身于韓國貴族,曾與李斯一道求學于荀子。韓非是戰國末年傑出的思想家,他推崇法家學說,主張修明法制,富國強兵。見韓國日漸貧弱,多次向韓王上書獻策,但不得信用,于是發憤著書立說。他的著作流傳到秦國,秦王(即後來的秦始皇)見了非常賞識,特意發兵攻韓,要他到秦國去。韓非出使到了秦國,卻未能受到信用,後來竟被李斯等人陷害,死于獄中。
韓非是先秦法家集大成的代表人物。他綜合了前輩法家的各種觀點,吸取了荀子和道家的某些理論,建立了以“法”為中心的“法、術、勢”三者合一的法家思想體系。他反對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張君主集權,任法而不任賢,崇尚功利,獎勵耕戰。主張“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具有進步的曆史觀。他提出在發展農業生産的基礎上用武力兼并六國統一天下的政見,被秦始皇采納并實行。
《韓非子》一書集中彙編了韓非的著作。它是先秦法家集大成的一部重要典籍,是在“百家争鳴”的高潮中産生的一部豐富多彩的學術巨著。今傳《韓非子》共55篇,基本上是韓非所著,但其中也有少數篇章為後學輯錄,故與先秦其他子書一樣,仍屬一家之學。與法家的刻深寡恩、真率直露的特點相适應,韓非的文章具有峻急、鋒芒畢露的風格。其文說理精密,文筆犀利,直言暢論,透徹明晰,又善于運用大量的寓言故事和曆史資料進行說理,在先秦諸子之文中自成一家,獨具特色。
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決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于夏後氏之世者,必為鲧禹笑矣;有決渎于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于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複得兔,兔不可複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财有餘,故民不争。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财貨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争。雖倍賞累罰而不免于亂。
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股無胈,胫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下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窦。故饑歲之春,幼弟不;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奪,非鄙也,财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争士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備适于事。
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裡,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裡,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幹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矩者及乎敵,铠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幹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争于氣力。齊将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裡以為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于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辔策而禦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于勢,寡能懷于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内,海内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勢,乘勢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而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谯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于愛、聽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铄金百溢,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乎,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随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
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缪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習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人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于君而曲于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奸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緻社稷之福,必不幾矣。
古者蒼颉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厶”,背厶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颉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仁義而習文學。仁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兼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
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論,則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貞信之行者,必将貴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群官無奸詐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于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為辯而不周于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亂;行身者競于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處岩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為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以境内之民,其言談者必軌于法,動作者歸之于功,為勇者盡之于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則不然,士民縱恣于内,言談者為勢于外,外内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從衡之黨,則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玺而請兵矣。獻國則地削,效玺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伐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于内,救小則以内重求利于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于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遊說之士孰不為用繳之說而徼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于内,而事智于外,則不至于治強矣。
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于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于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于從,衛亡于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緻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于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于内而政亂于外,則亡不可振也。
民之故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于敵,退則死于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
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遊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舍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貨賈得用于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緻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民多矣。
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談者,為設詐稱;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禦者,積于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财,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
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内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譯文
上古時代,人民少而禽獸卻很多,人類受不了禽獸蟲蛇的侵害。有位聖人出現了,在樹上做巢居住以避免獸群的侵襲,人民很愛戴他,便推舉他做帝王,稱他為有巢氏。當時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實和蚌肉蛤蜊,不但有腥臊難聞的氣味,而且傷害腸胃,人民經常患病。有位聖人出現了,鑽木取火來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愛戴他,便推舉他做帝王,稱他為燧人氏。中古時代,天下發大水,鲧和禹疏通了入海的河流。近古時代,夏桀和商纣殘暴淫亂,商湯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在夏朝有人還在樹上架木築巢,還鑽木取火,一定會被鲧、禹恥笑;如果有人在商朝還竭力疏導河流,一定會被商湯、周武王恥笑了。這樣說來,那麼如果有人在今天還贊美堯、舜、湯、武、禹的政治措施,一定會被新時代的聖人恥笑了。因此聖人不要求效法古代,不取法所謂永久适用的制度,而應研究當前社會的實際情況,并根據它制定相應的措施。宋國有個農民在地裡耕田,田裡有個樹樁子,一隻奔跑的兔子撞在樹樁上,碰斷脖子死了;這個人便因此放下手裡翻土的農具,守在樹樁子旁邊,希望再撿到死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可是他本人卻被宋國人笑話。今天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策來治理當代的人民,那就是守株待兔一類的人。
古時男子不須耕種,野生的果實就足夠食用;婦女不須紡織,禽獸的毛皮就足夠穿着。不用力勞作,生活資料就很充足,人民少但财物有多餘,所以人民之間不争鬥。因此不需要厚重的賞賜,也不需要嚴重的懲罰,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現在一個人有五個兒子不算多,每個兒子又有五個兒子,這樣祖父沒死就有了二十五個孫子。因此人民多而财物缺少,辛苦勞作,生活資料卻很貧乏,所以人民發生争鬥。即使加倍獎賞和加重懲罰,還是不能避免紛亂。
堯統治天下的時候,他的住房簡陋,屋頂上蓋的茅草未加以修剪,做椽子的栎木也沒有經過任何砍削加工;吃粗糙的糧食,喝野菜煮的羹湯;冬天穿小鹿皮做的袍子,夏天穿葛布做的衣服;即使現在的看門人,吃穿都不會比這更差了。禹統治天下的時候,拿着農具,親自率領民衆幹活,累得大腿上沒有肌肉,小腿上不長毛;即使現在奴隸的勞動都不會比這更苦了。按這樣的情況推論,古代讓出天子地位的人,好比是脫離看門人的生活,擺脫奴隸的勞苦,所以把天下傳給别人并不值得稱贊。今天的縣官,一朝死了,子孫世世代代還可乘車,所以人們看重官職。因此人們對于讓位的事,可以輕易辭去古代天子的地位,卻難以丢掉現在縣令的地位,其原因是利益大小的實際情況不相同。居住在山上卻要下到溪谷打水的人,每逢酒食宴飲的節日都把水作為貴重禮物相互贈送;在沼澤低窪地區居住苦于水患的人,卻要雇工挖溝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自己的親弟弟來了也不提供飯食;豐年秋收時,疏遠的客人也招待他吃飯。這不是疏遠骨肉兄弟而愛護過路客人,而是由于糧食多少的實際情況不相同。因此古人輕視财物,不是因為仁愛,隻是因為财物多;現在人們的争奪,也不是因為貪吝,而是因财物太少。古人輕易辭掉天子,不是品德高尚,是因為天子之位權勢微薄;今人看重并争取做官和依附權勢,不是品格卑下,是因為官位的權勢太重。所以聖人要研究社會财富多少、考慮權勢大小來制定他的政策。所以說古代刑罰輕不算仁慈,現在責罰嚴也不算殘暴,要适應社會習俗而行事。因此情況随着不同時代而變化,政策措施也要适應不斷發展的情況。
古時周文王住在豐、鎬一帶,土地隻有方圓百裡,施行仁義的政治,用安撫的手段使西戎歸附了自己,終于統一了天下。徐偃王住在漢水以東,土地有方圓五百裡,施行仁義的政治,向他獻地朝貢的國家有三十六國;楚文王怕他危害到自己,起兵攻打徐國,便滅亡了徐國。所以周文王施行仁義的政治終于統治天下,徐偃王施行仁義的政治卻亡掉了自己的國家,這說明仁義的政治隻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說:時代變了,情況也不同。在舜統治天下的時候,苗族不歸順,禹準備去征伐它,舜說:“不行。我們崇尚德教還不夠,卻施行武力,這不是治國的正道。”于是用了三年時間進行德教,手持盾牌大斧等兵器跳起舞來,以德服之,苗族才歸順了。在對共工的戰鬥中,手持加長了的鐵就能打到敵人,誰的铠甲不堅固就會受傷,這說明持盾牌大斧跳舞來降服敵人的辦法隻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說:情況變了,措施也要相應變化。上古時代人們在道德上争勝,中世時人們在智謀上角逐,當今時代卻在力量上較量了。齊國準備進攻魯國,魯國派子貢去說服齊國。齊國人說:“你的話不是不動聽,可是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所說的這一套空話。”便起兵攻打魯國,把邊境推進到距離魯國都門十裡的地方。所以說偃王施行仁義而徐國滅亡,子貢機智善辯而魯國的國土削減。從這方面來講,施行仁義和機智善辯,都不是用來保持國家的辦法。抛掉偃王的仁義,不要子貢的機變,憑借徐國、魯國自己的實力,來抵抗擁有萬輛兵車的大國,那末齊、楚兩國的欲望不可能在徐、魯兩國得逞了。
古今社會風俗不同,新舊政治措施也不一樣。如果想用寬大和緩的政策去治理昏亂時代的民衆,就好比沒有缰繩和鞭子卻要去駕馭烈馬一樣,這就會産生不明智的禍害。現在,儒家和墨家都稱頌先王,說他們博愛天下一切人,就如同父母愛子女一樣;用什麼證明先王如此呢?他們說:“司寇執行刑法的時候,君主為此停止奏樂;聽到罪犯被處決的報告後,君主難過得流下眼淚。”這就是他們所贊美的先王。如果認為君臣關系能像父子關系一樣,天下必能治理得好,由此推論開去,父子之間的糾紛就不會存在。從人類本性上說,沒有什麼感情能超過父母對于子女的摯愛,然而大家都一樣疼愛子女,家庭卻未必和睦。君主即使深愛臣民,何以見得天下就不會發生動亂呢?何況先王的愛民不會超過父母愛子女,子女不一定不背棄父母,那麼民衆何以就能相安無事呢?說按照法令執行刑法,而君主為之流淚,這不過是用來表現仁愛罷了,卻并非用來治理國家的。流淚而不願意用刑,這是君主的仁愛,然而不得不用刑,這是國家的法令。先王首先要執行法令,并不會因為同情而廢去刑法,那麼不能用仁愛來治理國家的道理也就明白無疑了。況且人們一向就屈服于權勢,很少能被仁義感化的。孔子是天下的聖人,他修養身心,宣揚儒道,周遊列國,可是天下贊賞他的仁、頌揚他的義并肯為他效勞的人才七十來個。可見看重仁的人少,能行義的人實在難得。所以天下這麼大,願意為他效勞的隻有七十人,而倡導仁義的隻有孔子一個。魯哀公是個下等的君主,面南而坐,統治魯國,國内的人沒有敢于不服從的。民衆,總是屈服于權勢,權勢也确實容易使人服從,所以孔子反倒做了臣子,而魯哀公卻成了君主。孔子并不是服從于魯哀公的仁義,而是屈服于他的權勢。因此,要講仁義,孔子就不會屈服于哀公;憑借權勢,哀公卻可以使孔子俯首稱臣。現在的學者們遊說君主,不是要君主依靠可以取勝的權勢,而緻力于宣揚施行仁義就可以統治天下,這就是要求君主一定能像孔子那樣,要求天下民衆都像孔子門徒,這是肯定不能實現的。
現在假定有這麼一個不成材的兒子,父母對他發怒,他并不悔改;鄉鄰們加以責備,他無動于衷;師長教訓他,他也不改變。父母的慈愛、鄉鄰的善意、師長的智慧這三方面同時加在他的身上,結果卻是他不受任何觸動,依然不改。直到地方上的官吏拿着武器,依法搜捕壞人的時候,他這才害怕起來,改掉了他舊日的習氣和不良行為。所以父母的慈愛不足以教育好子女而必須依靠官府執行嚴厲的刑法,這是由于人們總是嬌縱于慈愛而屈服于威勢的緣故。因此,七丈高的城牆,就連善于攀高的樓季也不能越過,因為太陡;千丈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可以上去,因為坡度平緩。所以明君總要嚴峻立法并嚴格用刑。一般人(拾到)十幾尺布帛都愛不釋手;可是燒得熔化的黃金,哪怕有兩千兩,就是盜跖也不敢去撿。不一定有惡果的時候,十幾尺的布帛也不肯丢掉;肯定會燒傷手時,就是兩千兩的黃金也不敢去拿。所以明君一定要嚴格執行刑罰。因此,施行獎賞最好是豐厚而且兌現,使人們有所貪圖;進行刑罰最好嚴厲而且肯定,使人們有所畏懼;法令最好是一貫而且固定,使人們都能明白。所以君主施行獎賞不随意改變,執行刑罰不輕易赦免,對受賞的人同時給予榮譽,對受罰的人同時給予譴責,這樣一來,不管賢還是不賢的人,都會盡力而為了。
現在就不是這樣。正是因為他有功勞才授予他爵位的,卻又因為他做官而看不起他;因為他從事耕種才獎賞他,卻又因為他經營财産看不起他;因為他不肯效命而疏遠他,卻又推崇他不羨慕世俗名利;因為他違犯禁令才給他定罪,卻又稱贊他勇敢。貶斥與贊美,獎賞與懲罰,執行起來竟如此自相矛盾,所以法令遭到破壞,民衆更加混亂。現在假如自己的兄弟受到侵犯就一定幫他反擊的人,被認為是正直;知心的朋友被侮辱就馬上去報仇的人,被認為是忠貞。這種正直和忠貞的風氣形成了,而君主的法令卻被冒犯了。君主推崇這種忠貞正直的品行,卻忽視了他們違犯法令的罪責,所以人們敢于逞勇犯禁,而官吏制止不住。對于不從事耕作就有吃有穿的人,說他有才能;對于沒有軍功就獲得官爵的人,說他有道德。這種道德和才能養成了,就會導緻國家兵力衰弱、土地荒蕪了。君主贊賞這種道德和才能,卻忘卻兵弱地荒的禍害,結果私人的品行得以确立,而國家的利益卻喪失了。
儒家利用文章學術擾亂法紀,遊俠使用武力違犯國家禁令,而君主卻都要加以禮待,這就是國家混亂的根源。犯法的本該判罪,而那些儒生卻靠着文章學說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該處罰,而那些遊俠卻靠着充當武士得到豢養。所以,法令禁止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處罰的,成了權貴豢養的。法令禁止和君主重用,官吏處罰和權貴豢養,四者互相矛盾,而沒有确立一定标準,即使有十個黃帝,也不能治好天下。所以對于宣揚仁義的人不應當加以稱贊,如果稱贊了,就會妨害事業的成功;對于從事文章學術的人不應當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會破壞法治。楚國有個叫直躬的人,他的父親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兒告發,令尹說:“殺掉他!”認為他對君主雖算無私而對父親卻屬大逆不道,結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來,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親的逆子。魯國有個人跟随君主去打仗,屢戰屢逃,孔子向他詢問原因,他說:“我家中有年老的父親,我死後就沒人供養他了。”孔子認為這是孝子,便推舉他做了官。由此看來,父親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殺了直躬,楚國的壞人壞事就再沒人向上告發了;孔子獎賞逃兵,魯國人作戰就會輕易地投降逃跑。國家和個人的離異像這樣不同,而君主卻一面贊成這種謀求私利的個人行為,一面又想求得國家的繁榮富強,這是一定不能如願的!
古時候,蒼颉創造文字,把圍着自己繞圈子的叫作“私”,與“私”相反的叫作“公”。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蒼颉就已經知道的。現在還有人認為公私利益相同,這是沒有仔細考察的過錯。那麼為個人打算的話,沒有什麼比講求仁義、學習文章學術的辦法更好。講求仁義就會得到君主信任,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熟悉學術就可以成為高明的老師,成了高明的老師就會得到名望和榮譽:對個人來說,這是最好的事。然而沒有功勞的就能做官,沒有爵位就能榮耀,形成這樣的政治局面,國家就一定陷入混亂,君主就一定面臨危險了。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殺敵有功的人本該受賞,卻又崇尚仁愛慈惠的行為;攻城立功的人本該授予爵祿,卻又信奉兼愛的學說;采用堅固的铠甲、鋒利的兵器來備戰,卻又提倡寬袍大帶的服飾;國家富足靠農民,打擊敵人靠士兵,卻又看重從事文章學術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養遊俠刺客之類的人:這樣的政治措施,要想使國家太平和強盛是不可能的。國家太平的時候供養儒生和遊俠,危難來臨的時候依靠披堅執銳的士兵;國家給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國家所要用的人,而國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處。結果從事耕戰的人荒廢了自己的事業,而遊俠和儒生卻一天天多了起來,這就是社會陷于混亂的原因所在。
況且社會上所說的賢,是指忠貞不欺的行為;所說的智,是指深奧玄妙的言辭。那些深奧玄妙的言辭,就連最聰明的人也難以理解。現在制定普通民衆都得遵守的法令,卻采用那些連最聰明的人也難以理解的言辭,那麼民衆就無法弄懂了。所以,連糟糠都吃不飽的人,是不會追求精美飯菜的;連粗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會期望有刺繡的華麗衣衫的。治理國家的政事也一樣,如果緊急的事情還沒有辦好,那麼可從緩的就不必忙着去辦。現在用來治理國家的政治措施,凡屬民間習以為常的事或衆人皆知的道理都不加以采用,卻去追求連最聰明的人都難以理解的說教,其結果隻能是适得其反了。所以那些深奧玄妙的言辭,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至于推崇忠貞信義的品行,必将尊重那些誠實不欺的人;而誠實不欺的人,也沒有什麼使别人不搞欺騙的辦法。平民之間彼此交往,沒有财富可以互相利用,沒有權勢可以互相威脅,所以才要誠實不欺的人。如今君主處于控制一切人的權勢地位,擁有整個國家的财富,完全有條件掌握重賞嚴罰的權力,可以運用各種駕馭臣下的方法和手段來觀察和處理問題,那麼即使有田常、子罕一類的臣子也是不敢欺騙君主的,何必尋找那些誠實不欺的人呢?現今的誠實不欺的人不滿十個,而國家需要的官吏卻數以百計;如果一定要任用誠實不欺的人,那麼合格的人就不夠分派官職;合格的人不夠分派官職,那麼能夠把政事辦好的官就少,而會把政事搞亂的官就多了。所以明君的治國方法,在于專一實行法治,而不尋求有智的人;牢牢掌握駕馭臣下的手段,而不指望得到忠信的人。這樣,法治就不會遭到破壞,而官吏們也不敢胡作非為了。
現在君主對于臣下的言論,隻求動聽而不管是否恰當;對于臣下的行事,隻慕虛名而不考察他們辦事的功效。因此天下很多人說起話來總是誇誇其談,卻根本不切合實用,結果弄得稱頌先王、高談仁義的人充滿朝廷,而政局仍不免于混亂;立身處世的人競相以清高相标榜,卻不為國家建功立業;結果有才智的人隐居山林,推辭俸祿而不接受,而兵力仍不免于削弱。兵力不免于削弱,政局不免于混亂,這究竟是怎麼造成的呢?因為民衆所稱贊的,君主所尊崇的,都是些使國家混亂的做法。現在全國的民衆都在談論如何治國,每家每戶都藏有商鞅和管仲論法治的書,國家卻越來越窮,原因就在于空談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農具種地的人太少。全國的民衆都在談論如何打仗,每家每戶都藏有孫子和吳起的兵書,國家的兵力卻越來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談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陣的人太少。所以明君隻使用民衆的力量,不聽信高談闊論;獎賞人們的功勞,堅決禁止那些無用的言行;這樣民衆就會拼命為君主出力。耕種是需要花費氣力吃苦耐勞的事情,而民衆卻願意去幹,因為他們認為可以由此達到富足。打仗是十分危險的事情,而民衆卻願意去幹,因為他們認為可以由此取得顯貴。如今隻要擅長文章學術,能說會道,無需耕種的勞苦就可以獲得富足的實惠,無需冒打仗的危險便可以得到尊貴的官爵,那麼誰不樂意呢?結果就出現了一百個人從事于智謀活動,卻隻有一個人緻力于耕戰的情形。從事于智謀活動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壞;緻力于耕戰的人少了,國家就會變得貧窮。這就是社會所以混亂的原因。
因此,在明君的國家裡,沒有文獻典籍,而以法令為教本;禁絕先王的言論,而以官吏為老師;沒有遊俠刺客的兇悍,而以殺敵立功為勇敢。這樣,國内民衆的一切言論都必須遵循法令的規定,一切行動都必須歸結于對國家有功,一切勇敢都必須用到從軍打仗上。正因如此,太平時期國家就富足;戰争時期兵力就強盛,這就積累了稱王天下的資本。既然擁有稱王天下的資本,又善于利用敵國的可乘之機,那麼超過五帝、比肩三王,一定得采用這種辦法。
現在卻不是這樣。儒士、遊俠在國内恣意妄為,縱橫家在國外培植自己的勢力。内外形勢都在惡化,就這樣來對付強敵,不是太危險了嗎?所以那些談論外交事務的臣子們,不是屬于合縱或連橫中的一派,就是内心懷有借國家力量來報私仇的隐衷。所謂合縱,就是聯合衆多弱小國家去攻打一個強大國家;所謂連橫,就是依附于一個強國去攻打其他弱國,這都不是保全國家的好辦法。現在那些主張連橫的臣子都說:“不依附大國,一遇強敵就得遭殃。”侍奉大國不一定有什麼實際的好處,倒必須先獻出本國地圖,呈上本國的玺印,一切聽命于大國。獻出地圖,本國的疆域就縮小了;呈上玺印,君主的聲望就降低了。疆域縮小,國家就削弱了;聲望降低,政治上就混亂了。侍奉大國實行連橫,還來不及看到什麼好處,卻已喪失了國土,搞亂了政治。那些主張合縱的臣子都說:“不救援小國去進攻大國,就失了各國的信任。失去了各國的信任,國家就面臨危險;國家面臨危險,君主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國不一定有什麼實惠可言,倒要起兵去和大國為敵。援救小國未必能使它保存下來,而進攻大國未必就不有閃失;一有失誤,就要被大國控制了。出兵的話,軍隊就要吃敗仗;退守的話,城池就會被攻破。援救小國實行合縱,還來不及看到什麼好處,卻已使國土被侵吞,軍隊吃敗仗。所以,侍奉強國,隻能使那些提倡連橫的臣下憑借外國勢力在國内撈取高官厚祿;援救小國,隻能使那些主張合縱的臣下憑借國内勢力從國外得到好處。國家利益沒有确立起來,而臣下反倒先把封地和厚祿都弄到手了;君主地位降低了,而臣下地位反而擡高了;國家土地削減了,而私家反而變富了。事情如能成功,縱橫家們就會倚仗權勢長期受到重用;事情失敗的話,縱橫家們就會憑借富有回家享福。君主如果聽信那些鼓吹合縱連橫的臣下的遊說,事情還沒辦成就已給了他們很高的爵位俸祿,事情失敗得不到處罰,那麼,那些遊說之士誰不願意用獵取功名富貴的花言巧語不斷去進行投機活動呢?所以國破君亡局面的出現,都是因為聽信了縱橫家的花言巧語造成的。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不考察言論是否正确,事敗之後也沒有堅決地實行處罰。縱橫家們都說:“進行外交活動,收益大的可以成就帝王事業,小國可以獲得安全。”大國既然可以成就帝王事業,便有能力攻打别國;小國既然可以保證安全,就不可能受到别國侵犯。國力強盛就攻打别國,政治清明就不可能被别國侵犯。而國家的強盛和安定并不能通過外交活動取得,隻能靠搞好内政。現在不在國内推行法術,卻把心思和智慧都用在外交上,就必然達不到國家安定富強的目的了。鄉間諺語說:“衣袖長,好舞蹈;本錢多,好買賣。”這就是說,資本越雄厚就越容易取得成功。所以政治清明、國家強盛,謀事就容易成功;國家衰弱、政治混亂,計策就難以實現。所以為“治強”的秦國謀畫,即使改變十次也很少失敗;而為“弱亂”的燕國謀畫,即使改變一次也很難成功。這并不是被秦國任用的人智慧必高,被燕國任用的人腦子必笨,而是因為這兩個國家的治亂條件大不相同。所以西周背棄秦國參予合縱,隻一年工夫就被秦國吞并了;衛國背離魏國參與連橫,僅半年工夫就被魏國消滅了。這就是說合縱滅了西周,連橫亡了衛國。假使西周和衛國不急于聽從合縱連橫的計謀,而将國内政治嚴加整頓,明定法律禁令,信守賞罰制度,努力耕種來增加财富,使人民拼死去堅守城池,那麼,如果别的國家即使獲得他們的國家也好處不多,而進攻他們的國家還傷亡很大。擁有萬乘兵車的大國也不敢在堅固的城池之下拖垮自己,以至于使自己的強敵乘此時的疲敝加以攻擊,這才是保證本國必然不會滅亡的辦法。丢掉這種必然不會亡國的辦法,卻去施行勢必會招緻亡國的事情,這是治理國家的人的過錯。外交陷于困境,内政陷于混亂,那麼國家的滅亡就無法挽救了。
人們的習慣想法,都是追求安逸和私利而避開危險和窮苦。如果讓他們去打仗,前進會被敵人殺死,後退要受軍法處置,這就處于危險之中了。放棄個人的家業,承受作戰的勞苦,家裡有困難而君主不予關照,這就處于窮困之中了。窮困和危險交加,民衆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們争相為貴族豪門服勞役,替他們修繕房舍,以求免除兵役,這樣就可以遠離戰争,也就可以得到安全了。用錢财賄賂當權者就可以達到個人欲望,欲望一旦達到也就得到了實際利益。安全并且有利的事情明擺在那裡,民衆怎能不去追求呢?這樣一來,為公出力的人就少了,而依附私門的人就多了。
明君治理國家的政策,總是要使工商業者和遊手好閑的人盡量減少并且地位卑下,以免從事農耕的人少而緻力于工商業的人多。現在向君主的近臣請托求情的風氣很流行,這樣官爵就可以用錢買到;官爵可以用錢買到,那麼工商業者的地位就不會低賤了。投機取巧非法獲利的活動可以在市場上獲利,那麼商人就不會少了。他們搜括到的财富超過了農民收入的數倍,他們獲得的尊貴地位也遠遠超過從事耕戰的人,結果品行端正的人就越來越少,而經營商業的人就越來越多。
因此,造成國家混亂的風氣是:那些著書立說的人,稱引先王之道來宣揚仁義道德;講究儀容服飾而文飾巧辯言辭,用以擾亂當今的法令,從而動搖君主的決心。那些縱橫家們,弄虛作假,招搖撞騙,借助于國外勢力來達到私人目的,不惜抛棄國家利益。那些遊俠刺客,聚集黨徒,标榜氣節,以圖顯身揚名,結果觸犯國家禁令。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依附權臣貴族,肆意行賄,而借助于重臣的請托,逃避服兵役的勞苦。那些工商業者,制造粗劣器具,積累财富,囤積居奇,希圖從農民身上牟取暴利。上述這五種人,都是國家的蛀蟲。君主如果不除掉這五種像蛀蟲一樣的人,不網羅品行端正的人,那麼,天下即使出現破敗淪亡的國家,地分國滅的朝廷,也不足為怪了。
影響與傳播
先秦諸子大都是古非今,貴古賤今。韓非則不同。他也講曆史,但他着眼于曆史的不斷變動,論述法治應當适合時代的要求,并提出實際的權勢比空頭的仁義更有效,反對政治上頑固守舊的态度。明确提出了古今有異,“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的觀點,認為“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這種反對複古,主張革新;反對因循舊制,主張因時而變的思想,反映了進步的社會曆史觀,體現了新興地主階級改革舊制度的進取精神,一直為人們所激賞。但是,把曆史的發展說成是少數聖人的創造,把社會鬥争的根源歸為人口多而财物少等觀點,是有局限性的。
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之中,儒、道、墨、名、農、陰陽等各家盡管大家輩出,但與政治哲學相結合,使書齋式的理論探讨經受住了殘酷政治鬥争考驗的似乎隻有韓非子一家。韓非主張在發展農業生産的基礎上進行兼并戰争,以武力統一中國,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這迎合了統治者急功近利的心理,成為秦始皇治國政策的首選。《史記》韓非本傳記載:“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由此可見韓非學說的切于實用。他的耕戰理論成為秦朝統治天下的重要理論依據,對秦王朝一統天下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專家點評
選自《韓非子》,《五蠹》是其中的第一篇,也是體現韓非政治思想的重要篇章。
“五蠹”就是五種蛀蟲。作者認為,“學者”(儒家)、“言談者”(縱橫家)、“帶劍者”(遊俠)、“患禦者”(害怕服公役的人)、“商工之民”(經商做工的人)是實行耕戰政策以富國強兵的破壞力量,因而把他們比作危害國家的五種蛀蟲。
作者認為:“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争于氣力”,因而反複申述“事因于世,而備适于事”。鑒于當時的時代是“急世”,因此不能用仁義來治理國家,而要以耕戰為立國之本。凡是無助于耕戰的,如“學者”(儒家)“言談者” (縱橫家)、“帶劍者”(遊俠)、“患禦者”(害怕服公役的人)、“商工之民”(經商做工的人)都是國家的蛀蟲。韓非認為要使國家富強,君權鞏固,必須“除此五蠹之民”,“養耿介之士”。并具體到“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人主如果“不除此五蠹之民”,亡國滅朝也就不足為怪的結論。
文章指出:“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顯然,韓非的耕戰方針和嚴刑峻法政策是一種戰時的權宜之計。韓非死後十幾年,秦始皇統一了天下,其仍然推行韓非那一套嚴刑峻法政策,這不能不說是一大失誤。而且韓非提倡變法目的在于使專制君王牢牢地把持權力,維護最高統治者的既得利益。圍繞這個目的,他的談變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為反傳統、搞權術、飾非拒谏尋找托詞。後來秦二世在和趙高的君臣對談中,就曾經引用韓非《五蠹》來為自己的窮奢極欲、殘害百姓辯護。因此,秦的迅速滅亡,也跟推行韓非的那一套理論脫不了幹系。韓非與秦朝的興亡真是結下了不解之緣,堪稱是“成也韓非,敗也韓非”!
本篇運用先擺事實,後講道理的方法,由遠而近,從古到今,自淺入深,從具體到抽象,層層深入,論證深刻周密,文風峻刻犀利,具有難以抗拒的說服力。文中寓言的運用和史事的引述,都有助于以具體的形象說明抽象的道理。議論中常引用寓言故事來說理,也增強了文章的生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