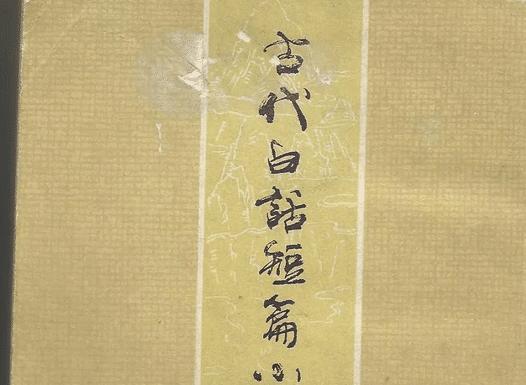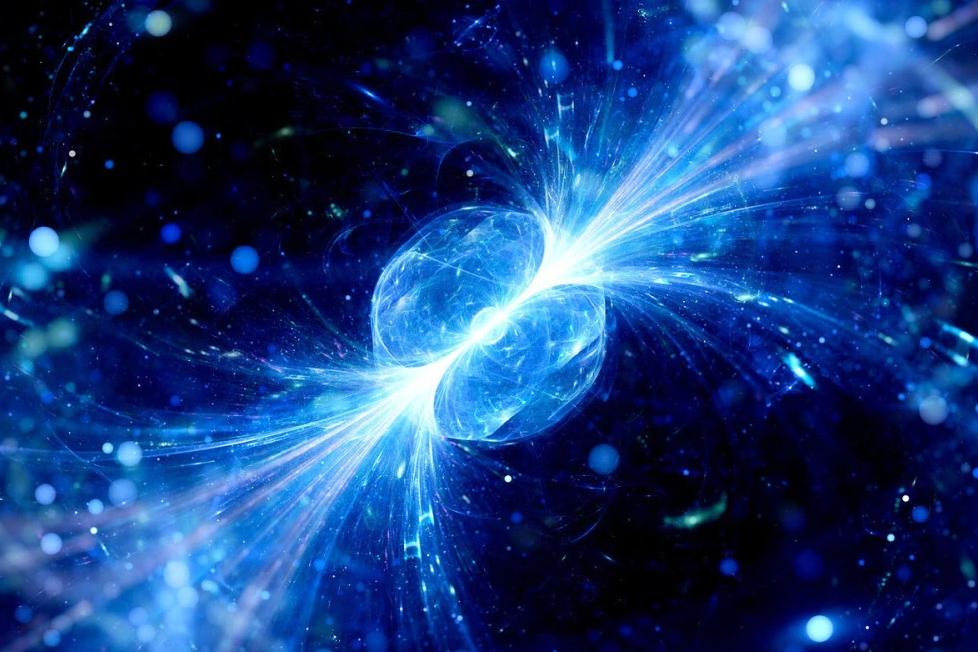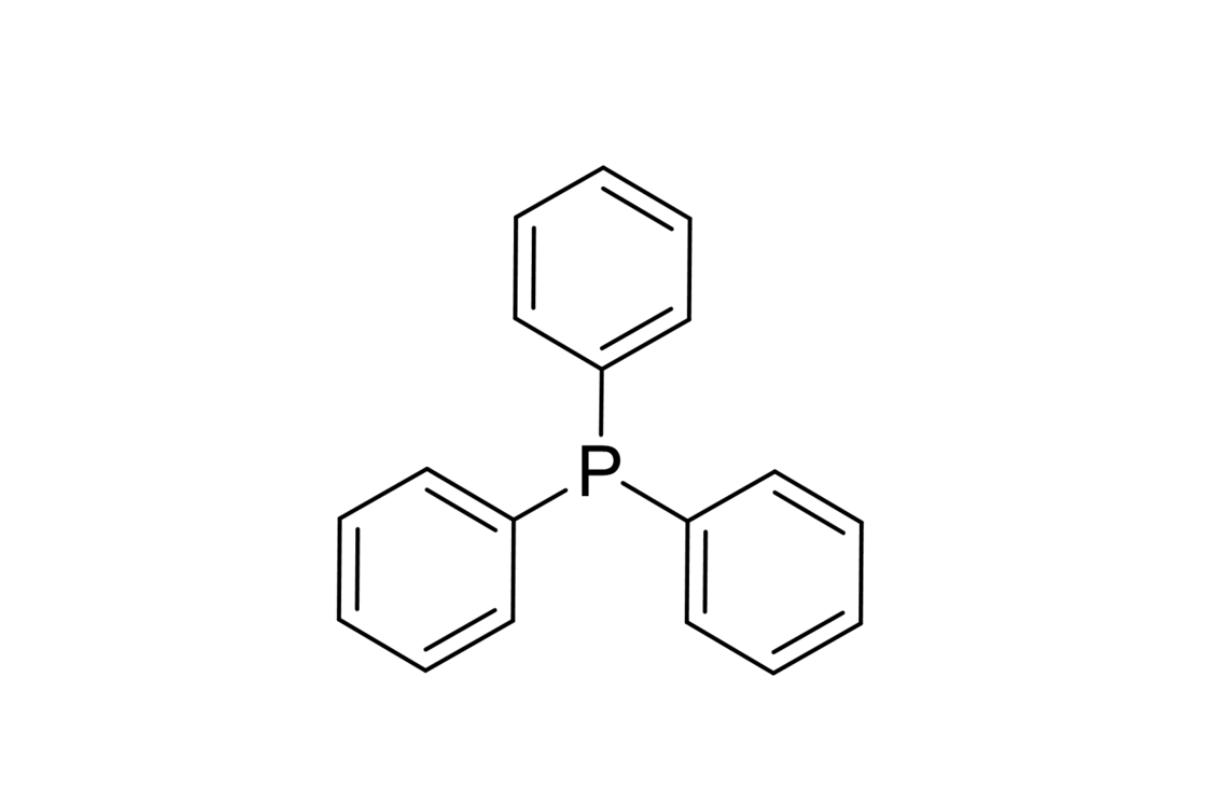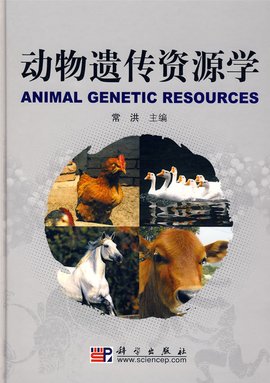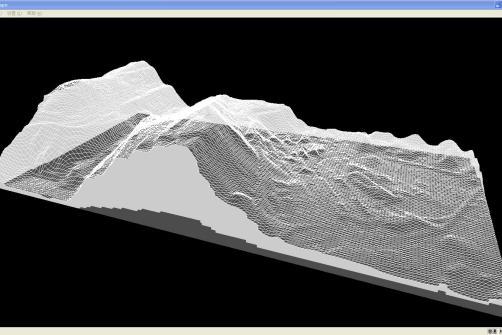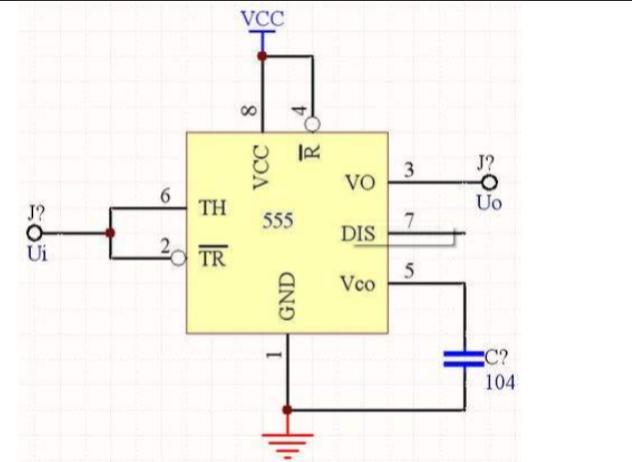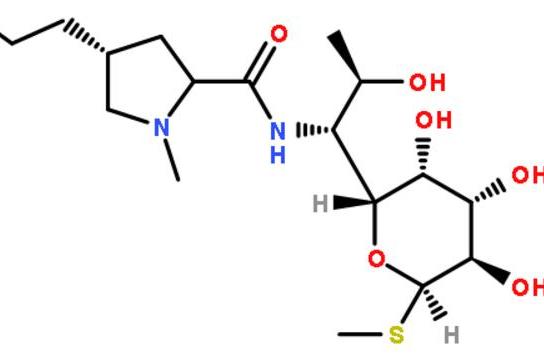發展源流
1.發祥期:唐代
當時,市人小說、寺院俗講成為白話小說的兩個發展源頭。
2.黃金期:宋、元時期,開封、杭州等瓦舍勾欄處,“說話”藝術盛行,由此産生“話本小說”。這也是最早的白話小說形式,這種小說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短篇白話故事,篇幅較短,基本用口語叙述,有虛構性。
3.宋末及元代,在白話小說基礎上出現了文人模仿此形式創作的拟話本小說。
3.全盛期:明、清
這一時期,産生了演義小說、長篇章回體小說等。如明代四大奇書:《水浒傳》《三國演義》《西遊記》《長篇章回體演義小說》《金瓶梅》;明代的拟話本小說“三言”“兩拍”;“三言”即馮夢龍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即淩蒙初”的《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清代“雙峰”:《儒林外史》《紅樓夢》。而《紅樓夢》更成為中國古代現實主義小說輝煌的頂點。
白話小說
“小說”一詞最早出現于《莊子外物篇》:“飾小說以幹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這裡認為小說是一種不登大雅之堂、不為學士大夫所重視的東西。鄭振铎在《中國俗文學史》中說:“凡是不登大雅之堂、凡為士大夫所鄙夷、所不屑注意的文體都是‘俗文學’”,小說正是這樣一種俗文學。班固也認為“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他認為小說是末技,是小道小智所為。但小說的生命力極為旺盛,雖然飽經磨難和拒斥,卻仍然有強烈的發展勢頭。随着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到唐宋之交,漢族市民階層興起,尤其是宋代,生産力發展迅速,市民階層日益壯大,他們對文化生活的需求,休閑娛樂的呼喚也日益強烈,城市文化越來越盛行,中國的長篇白話小說以此為契機,迅速的發展起來。
唐代傳奇相對白話小說是雅,但拿傳統的雅俗觀來衡量它,卻又可以說它為俗。雅俗問題與上述娛樂和教化、虛構和實錄的問題有着内在的聯系。教化的内容是禮義,實錄叫做雅馴,可見傳統的雅俗觀是貶低和排斥娛樂和虛構的。儒家道統文統的繼承和發揚,阻塞了傳奇小說的發展。傳奇小說,一般的說是士人寫給士人讀的文學,它本來就産生和活躍在雅文化圈内。當它蒙上不雅的俗名,士人便疏遠它,它便從雅文化圈走出來,逐漸向俗文化靠攏。宋代傳奇小說作者的文化層次下移,同時創作傾向卻向雅的方向攀附。“論次多實”、“采豔殊乏”,都是棄俗而就雅的表現。
降至元明,傳奇小說俗化趨勢愈益明顯,從明代中後期流行的各種通俗類書如《國色天香》、《萬錦情林》、《繡谷春容》、《燕居筆記》等競相轉載來看,它們在士人中還是頗有讀者的。人們總愛附庸風雅,标榜不俗,而實際卻有難以脫俗的一面。
這類半文半白的、篇幅已拉得很長的傳奇小說繼續走着俗化的路,到明末清初,它們幹脆放棄文言,使用白話,并且采取章回的形式,便成為了才子佳人小說,完全與通俗小說合流。
如果說傳奇小說是從雅到俗,那麼白話小說的運動方向恰好相反,是從俗到雅。白話小說無論短篇還是長篇,都源于民間“說話”,它們的體制和叙事方式都保留着“說話”的胎記,與源于史傳的傳奇小說迥然有别。白話小說長時期在民間傳播,其故事是生鮮的、同時又是稚拙的,版刻也很粗率。直到明代嘉靖前後,情況才發生重大變化。文人突然看好這種俗而又俗的文學樣式,他們不隻是評論,而且參與其間,進行搜集、整理、加工、編輯、出版。接着還有模拟這種樣式的文人創作,如馮夢龍的“三言”,淩蒙初的“二拍”和陸人龍的《型世言》,等等。
這種情況的發生,與王陽明“心學”的崛起有着直接的關系。王陽明是主張人皆可以成為聖賢的,有利用俗的形式才能達到化俗的效果。他對俗的重視,在當時卻有振聾發聩效果。嘉靖萬曆時代推崇通俗文學的文學家所依據的就是王陽明的這種思想。
白話小說的作者由不見經傳的無名氏,漸次上升為大文人。他們的文化修養和社會地位都是早期白話小說作者所不能相比的。
白話小說的内容和風格也随着作者成份的改變而漸次由俗變雅。按創作方式,白話小說的演進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早期是“說話”的書面化;中期是作家根據現成故事進行創作;後期是作家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獨立創作。文人獨創的小說,不僅題材情節出自個人機杼,而且藝術風格也有鮮明的個性。白話小說發展到後期已有雅俗的分别。不過,白話小說的主流趨向于雅,卻是不争的事實。
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它們的源頭分别為雅和俗,它們的走向卻相反,文言小說向俗靠攏,白話小說向雅接近。雅俗在小說範疇内達成了妥協。“雅”接納了白話,承認了“虛構”;“俗”則承擔起“教化”的使命。換言之,“雅”放棄了“雅言”和“實錄”的原則,“俗”則放棄了娛樂惟一的宗旨。小說中雅俗共存是小說藝術成熟的重要際志。
中國小說的源頭就存在着雅俗的分歧,雅的是文言小說,它從史傳蛻化而來;俗的是白話小說,它從民間伎藝“說話”轉變而成。在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的發展途程中,雅和俗構成兩極,文言小說受到俗的引力作用,不斷吸收俗的成分,顯示出漸次俗化的傾向;而白話小說則受到雅的引力作用,不斷吸收雅的成分,表現為漸次雅化的傾向。雅俗結合是小說成就的重要标志之一。
明萬曆以後,不僅長篇小說的創作達到了空前的繁榮,而且短篇白話小說的創作也呈現出繁榮景象。
古典文言短篇小說作品衰微,這種文學樣式在當時已不适應社會的要求,相反,白話短篇小說作品的創作卻是一派生機盎然。這裡的原因是比較多的。首先,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城市不斷擴大,市民階層的力量壯大,在社會上是一股極為活躍的、強大的階層,他們要求在文學上能有反映他們的生活和思想的文學樣式和文學作品。
其次,宋元話本小說在明代得以繼續發展,它是勞動群衆小說創作自身發展的結果,顯示出比文言小說更強的生命力。參予白話小說創作的作家大多是中下層知識分子,他們善于吸收群衆藝術創作的結果,語言通俗易懂,作品更多地反映了現實社會的内容,有一定的社會批判精神,因而有着更強的人民性,為廣大群衆所觀賞喜愛。
明代印刷術發達,書壇衆多,迎合人們的口味與喜好,書商也大量地刊行話本小說,因此話本小說慢慢地演變為供案頭閱讀之作的拟話本。
拟話本的體裁與話本相似,都是首尾有詞,中間以詩詞為點綴,故事性強,情節生動完整,描寫人物的心理細緻入微,個性突出,比較注意細節的刻畫等。但它又與話本不同。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認為拟話本是“近講史而非口談,似小說而無捏合”,“故形式僅存,而精采遂遜。”在口語運用和生活氣息上,拟話本明顯地遜于話本小說。
現在認為最早的話本集《清平山堂話本》,是嘉靖年間洪楩輯印的,分《雨窗》、《長燈》等6集,每卷1篇,共收話本60篇,故全書總名為《六十家小說》,今存15種。萬曆年間熊龍峰刊印的話本今存4種。這兩種話本集都包括宋元話本和明代拟話本在内。天啟年間馮夢龍編輯的《喻世明言》(初題《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短篇小說集,簡稱“三言”,每集收話本40篇,包括宋元話本、明代拟話本兩部分。“三言”對後世影響較大,此後拟話本的專集大量出現。明末淩蒙初在“三言”的影響下,創作了《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兩個拟話本集,簡稱“二拍”。“三言”、“二拍”代表了明代拟話本的成就,是由話本向後代文人小說過渡的形态,對中國古典白話小說創作在明末以後繼續發展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明代白話短篇小說反映了廣泛的社會生活内容。愛情婚姻的題材是明代拟話本的一個重要内容。《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樂小舍拚生覓偶》、《玉堂春落難逢夫》等真實地描寫了被糟踐的婦女的悲慘地位以及她們對愛情婚姻的自主要求,對幸福生活的追求與向往,貫穿了對封建禮教及門第觀念的批判,尤其是《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藝術上,都可稱為古代白話短篇小說的代表作。在《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賣油郎獨占花魁》等篇中,反映了市民階層的愛情婚姻觀念。《俞伯牙摔琴哭知音》、《施潤澤灘阙遇友》等篇描寫了在冷酷的等級社會中真誠的友誼。《沈小霞相會出師表》、《盧太學詩酒傲王侯》、《灌園叟晚逢仙女》等篇暴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猙獰面目和無恥罪惡。《轉運漢巧遇洞庭紅,波斯胡指破鼍龍殼》、《疊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顯靈》等篇反映了明代社會商人的心理。
總之,揭露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和政治的黑暗,描寫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的生活與思想,歌頌市民階級的勤勞誠實及對發财緻富的追求,要求愛情與婚姻生活的自由,抨擊科舉制度的不合理和司法制度弊病等主題,共同組織成明中葉以後短篇白話小說的重要内容,顯示了明拟話本新的思想特色。但“三言”、“二拍”中也包含着明顯的落後和庸俗的因素,比如美化統治階級、宣揚封建禮教、迷信鬼神等占了相當的數量,尤其又以“二拍”更為嚴重,這也是明代後期話本小說的通病。明末短篇白話小說集還有十多種,比較有影響的是《西湖二集》、《石點頭》、《鼓掌絕生》、《醉醒石》等,成就都不高,但其中有一些篇章,文筆生動,形象鮮明,對封建社會的種種弊病有所揭露。
明清時代是一個充滿進步與守舊、啟蒙與頑愚、思想解放與鉗制的時代。一方面,個性覺醒,人本意識擡頭,不少進步人士張揚個性,追求自由,肯定物欲财利,這反映在小說裡就是小說中人性湧動,追求物欲,情愛描寫細膩等。另一方面,封建統治者強化統治,中央集權突出,進一步加強思想控制,由此也出現了一些理學觀念濃厚、倫理說教明顯的小說作品。此外,還有兩種思想皆有,禁欲主義和享樂之風并行。明清小說内容豐富,類别繁多。
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
1918年作者第一次以魯迅為筆名,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
《狂人日記》是魯迅的一篇短篇作品,收錄在魯迅的短篇小說集《呐喊》中。首發于1918年5月15日4卷5号《新青年》月刊。内容大緻上是以一個“狂人”的所見所聞,指出中國文化的朽壞。《狂人日記》寫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它是魯迅創作的第一個白話小說,也是現代中國的新文學的第一篇傑出作品。《狂人日記》的主題,據魯迅說,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弊害”何在?乃在“吃人”。魯迅以其長期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的深刻觀察,發出了震聾發聩的呐喊:封建主義吃人!魯迅曾說,《狂人日記》“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它以“‘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的确,《狂人日記》在近代中國的文學曆史上,是一座裡程碑,開創了中國新文學的革命現實主義傳統。
《狂人日記》的研究
其次,結合魯迅的創作情況來看,在魯迅的小說中,有一些作品不像《阿Q正傳》、《孔乙己》、《祝福》、《故鄉》等作品側重刻畫人物性格的外現(形貌、言行、履曆、事件等),而是以人物的内心及精神世界的某一因素的活動為主,展示其某一精神意識傾向,比如《狂人日記》、《白光》、《長明燈》、《傷逝》等。這類作品雖有人物的言行活動,但主宰作品的因素是某種精神意識。以《狂人日記》來看,小說開頭的第一部分就采用這樣文字: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見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見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發昏;然而須十分小心。不然,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
我怕得有理。
小說一開場,登場的是人物的意識,魯迅不用很亮很清之類的單一視覺的文字,而用“很好”這樣綜合意識來把握月光。接下來,“我”出場了,但對于讀者來說,“我”無形無狀,更不用說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年輕是年老,實質上,“我”即“我”的意識在繼續牽着讀者走:“我不見他,已是三十多年”是對“很好的月光”這種感覺的意識重認;“今天見了,精神分外爽快”這一句,是意識再次把握;“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發昏;然而須十分小心”,這是意識重認後新意識的出現;“不然,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新出現的意識開始把新的客觀對象納入意識範圍———注意,此處不是對趙家的狗那兩眼的客觀描述,而是意識對于這一事實的一種把握。“我怕得有理。”這一句,意識走向判斷。依此分析的路子,使之貫串整部小說,都不難得出意識流動的軌迹。因此,從這一視角看,《狂人日記》是一部展示意識過程的一部小說,簡單說,《狂人日記》是一部意識性小說。
再次,在小說的結尾,有這樣的一句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曆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魯迅此處冠以“我”有“四千年履曆”,并把“真的人”與“我”相對,暗示着“我”并非具體存在的人而是一種藝術設置,當然,“我”隻能是人,隻有人才能承載某種人的意識,但在《狂人日記》中,這個人又不會是真實的具體的“迫害狂”病人,魯迅作為藝術家不會像醫生和心理研究者那樣,去記錄描述一個病患者的征狀。在《狂人日記》中,假如從一個“迫害狂”患者的角度來看,魯迅對其所作的能充分表現這一患者的特征規定是極少的,“我”無名無姓,沒有病因解釋,沒有病史說明,所生活的環境和時代也有極寬的範圍。而另一方面,魯迅又極為精細傳神地把握“迫害狂”這類患者的共同特征。這說明,“我”作為一個具體存在并不重要,魯迅對于狂人的選擇并不在于這個狂人是誰,而是因為選擇狂人符合于魯迅的藝術設置和藝術表述,假如小說中的“我”是一個一般的人,那麼魯迅就無法在其身上表述“多疑”的這一意識。從小說的實際情況來看,“我”這一狂人所表現出來的病狀是“迫害狂”一類的共同特征。實際上,“我”隻是一個承載物。一方面,“我”承載着狂人所共有的病狀,以達到小說所要求的藝術真實的要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的病狀在某一層次上與作家所要表述的東西相吻合。而在具體的文本創作之中,作家不可能直裸裸地把自己的東西強加給作品中的人物,相反隻能是遵從所選擇的人物性格特點和發展規律,融入自己的東西。由于藝術選擇加上藝術家的藝術表述能力,魯迅的《狂人日記》一方面極為真實地描述了“迫害狂”的征狀言行,但另一方面又極為巧妙地昭示小說并不是要表現“迫害狂”的征狀,而是要表述狂人所承載的合乎狂人身份其實是作者自己的東西。也即魯迅之所以選擇狂人是因為狂人有顯着的“多疑”特征,它暗合着魯迅“多疑”意識的内核表述。所以魯迅選擇了狂人來承載“多疑”這一意識,作者着重要表現的不是這個人,而是這個“我”所承載的意識“多疑”。
經過這樣一番梳理,《狂人日記》這一部小說可以說是一部以狂人所承載的“多疑”并依據這一意識的某種特征展開的小說。
問題是:《狂人日記》中的“多疑”能夠與魯迅的“多疑”相聯系起來嗎?
這也是要談的第二個條件。
魯迅先生是一個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并以此去支配自己行動的人,這同樣也體現在其文本創作之中。魯迅曾一再強調作品中的自我意識:“我力避行文的唠叨,隻要覺得夠将意思傳給别人了,就甯可什麼陪襯拖帶也沒有。”“所寫的事迹,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隻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為止。”從寬泛意認上說,所有作家的作品都肯定包含着作家的精神意識世界的表述,但由于作家的藝術思維不同,其在具體的作品表現也不同。有時候,作品的客觀内容與作家表述的精神意識相互分離,有時候,作品的客觀内容與作家表述的精神意識融一。前者如《祝福》,透過《祝福》文本的客觀内容,可以把握到魯迅對于“祥林嫂”這類人物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而後者如《狂人日記》、《長明燈》、《過客》、《這樣的戰士》等,作者客觀上描寫某一人物某一事實,同時又把某種意識融入其中。舉個例子說,《狂人日記》中“從來如此,便對麼?”的诘問,可以是狂人的、也完全是魯迅先生的诘問。對于魯迅與《狂人日記》的關系,已逐漸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魯迅的幾乎所有的心理特征和表現,都能在《狂人日記》中一窺端倪。”“《狂人日記》中,那種‘迫害狂’式的病态心理,本身就是他(魯迅)切身體驗的‘變形記’。”“因此,‘狂人’實際上不僅僅是一個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義者,而且是一個文化先覺者形象,是魯迅反抗精神的形象外化。”這些看法都是中肯的,但沒有注意狂人形象與魯迅的差别。在《狂人日記》中,“多疑”這一意識的活動特征首先是歸屬于患“迫害狂”的狂人屬性,這些屬性是不能套在魯迅身上的,而狂人這一藝術設置及如何設置、對于“多疑”的表述,則是按着魯迅心靈對于“多疑”的解讀和描述實現的,同時對于“多疑”的解讀和描述,自然受着魯迅“多疑”的主體支配。因此,從《狂人日記》去把握魯迅的“多疑”成為可能,并具有重要意義,但要從中把握魯迅的“多疑”的本質及個性色彩,必須進入作品,并以一定的方法對狂人的多疑與魯迅的“多疑”加以分離。
古代白話小說的優秀代表作品
古代白話小說的優秀代表作品如《三國演義》、《水浒傳》、《西遊記》、《金瓶梅》、“三言”“二拍”《儒林外史》、《紅樓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