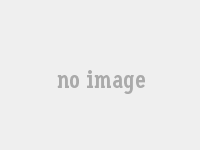人物生平
生而聰慧
乾隆十七年(1752年)九月二十二日,李祘生于昌慶宮景春殿,父親是王世子李愃,母親是世子嫔洪氏,還有一個在他出生前不久夭折的兄長懿昭世孫李琔。李祘出生前夜,父親思悼世子曾夢見一條龍進入寝室,醒來後就在景春殿東壁畫了一條龍,來紀念兒子誕生的喜事。
據其母洪氏所撰行錄記載,李祘自襁褓中就氣象伶俐、相貌不凡,因此洪氏受到祖父英祖李昑的稱贊,尤其是英祖看到李祘那高高的額頭和凸出的後腦勺更是喜不自勝,說李祘像自己。李祘在百日前就能站立,周歲前就能走,抓周時走向晬盤,先抓筆墨,然後翻開書看,舉止俨然,人們看到他這麼小就有與衆不同的資質,無不失色驚歎。而且年幼的他喜歡寫字,兩字就能寫字,三四歲就已具備筆畫的模樣,每日以寫字畫畫為樂,五六歲時寫的字就有被做成屏風的了。諺文則在四五歲就已通曉,據說能像成人一樣寫書劄了。

幼遭慘變
當時,李祘的父親思悼世子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火病),李祘雖然深受疼愛,但亦曾在一次問安中被父親的無端發怒所驚吓。 李祘因“夙成英明”,深得英祖喜愛,常常将李祘帶在身邊,并屢次于“筵席”(指君臣對話的地方)中公開贊揚李祘,而思悼世子則被英祖疏遠厭棄。代理聽政中的思悼世子可以閱覽“筵說”(英祖在“筵席”上的談話)記錄。世子嫔洪氏擔心思悼世子看到英祖稱贊李祘的話後心理失衡,會使他與李祘的父子關系産生裂痕,進而對李祘不利,便與父親洪鳳漢商量,讓内官将“筵說”中英祖誇贊李祘的話全部删除後再謄抄呈給思悼世子閱覽。盡管如此,李祘對思悼世子仍然“誠孝懇笃”“承顔順志”,當英祖和思悼世子之間發生沖突,他往往“委曲周旋”,努力化解。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二月,李祘被立為王世孫。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三月入學景賢堂,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春,行冠禮與嘉禮,迎娶金時默之女為王世孫嫔(後來的孝懿王後)。這一年閏五月,發生了祖父英祖将父親思悼世子關進昌慶宮徽甯殿的米櫃、最終活活餓死的“壬午禍變”。李祘曾進入徽甯殿,試圖救父,結果被英祖命人強行抱走。其後,英祖确立“壬午義理”,規定任何人不得給思悼世子翻案。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二月,又将李祘過繼給早夭的孝章世子李緈,使其不得承生父思悼世子之統。英祖下達這個變更宗統的“甲申處分”,一方面為了牽制李祘的外祖父洪鳳漢一家,以免他們将來追崇思悼世子為王;另一方面,也在宗法上将李祘與思悼世子調整為叔侄關系,使李祘能相對擺脫思悼世子之死所造成的正統性困擾。
這場人倫慘變對李祘來說是莫大的陰影。但母親洪氏為防止李祘重蹈思悼世子的覆轍,對李祘給予無微不至的關愛。洪氏沒有慫恿李祘為父報仇,反而教導李祘報答英祖的聖恩,這對李祘的成長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也避免了李祘成為第二個燕山君。此外,洪氏還将李祘托付給思悼世子生母映嫔李氏撫養,讓他在英祖身邊長大。映嫔死後,和緩翁主對李祘的影響逐漸增大,而李祘也因此對母家有所疏遠。
艱難嗣位
英祖末年的政局呈現出當權的洪麟漢、鄭厚謙等外戚勢力與标榜清論的“清名黨”官員對立的格局。洪麟漢雖身為李祘的外叔祖父,表面上也标榜保護世孫,但其實與鄭厚謙及其養母和緩翁主勾結,危害李祘。李祘周邊從侍從到奴仆,都有不少是洪麟漢、鄭厚謙安插的人,負責刺探李祘的動靜,李祘甚至長期穿着外衣睡覺,以防不測。另一方面,李祘先有外祖父洪鳳漢保護,洪鳳漢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受李祘的兩個異母弟恩彥君、恩信君連累而失勢,後來李祘又得到洪國榮、鄭民始等東宮僚屬的保護,同時亦與“清名黨”接近。
支持李祘與反對李祘兩股勢力的對立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達到極點。當時,英祖病症加重,李祘已代攝各種祭祀,英祖至十月更考慮讓李祘代理聽政。十一月二十日,他在召見左議政洪麟漢時問:“沖子(指李祘)知老論乎?知少論乎?知南人乎?知少(小)北乎?知國事乎?知朝事乎?知兵判誰可為、吏判誰可為乎?”洪麟漢回答:“東宮不必知老論、少論,不必知吏判、兵判。尤不必知朝事矣。”這被洪國榮等認為是阻止世孫代理聽政(李祘之母惠慶宮洪氏則予以否認,認為這隻是應付英祖的回答而已,洪麟漢并無謀害李祘、阻撓代理之意),便找到行副司直徐命善,讓他于十二月初三日上疏彈劾洪麟漢,英祖采納,罷免洪麟漢,随後命世孫代理聽政。十二月十日,李祘在景賢堂開始代理聽政。
他雖初出茅廬,但處理政事井井有條,朝鮮上下為之大悅。在此期間,他還請求英祖将壬午禍變的相關記錄“洗草”(銷毀),英祖不僅同意,還宣布“此後語及壬午事,當以逆律論”。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三月初五日,英祖薨逝于慶熙宮集慶堂。當時李祘正準備代英祖主持大報壇的春享大祭,聽到英祖死訊後不得不中止。三月初十日,李祘即位于慶熙宮崇政門,是為正祖。三月十九日,追尊養父孝章世子為真宗大王,養母孝純嫔趙氏為孝純王後。翌日,改谥思悼世子為莊獻世子,改垂恩墓為永祐園,并立景慕宮為其祠堂。三月二十五日,台谏開始彈劾鄭厚謙母子之罪,正祖将鄭厚謙流放至鹹鏡道慶源府。其後台谏又彈劾洪麟漢,正祖乃于四月七日下令流放洪麟漢于忠清道砺山府。六月三十日,百官請誅鄭厚謙、洪麟漢,數日後正祖下令将兩人賜死。此外,他還将曾攻擊過自己外祖父洪鳳漢的金龜柱(貞純王後之兄)流放黑山島,追奪危害過莊獻世子的前領議政金尚魯的官爵,賜死文女(廢淑儀文氏)。十月二十七日,接受清朝乾隆帝冊封為朝鮮國王(正使散秩大臣覺羅萬福、副使内閣學士嵩貴)。
鞏固統治
正祖雖然剛上台就清洗了反對勢力及曾陷害生父的相關人員,但還有一些殘餘勢力并未被清除,例如已故大臣洪啟禧就曾陷害過莊獻世子,但因無英祖下教而沒有追加處罰,隻以鄭厚謙、洪麟漢同黨的罪名流放其弟洪啟能、其子洪述海、洪趾海、洪缵海,其孫洪相簡則死于獄中。其後,洪啟禧之孫、洪述海之子洪相範企圖弑殺正祖,收買了扈衛廳軍官姜龍輝及其當宮女的女兒姜月惠、當掖隸(宮廷仆役)的侄子姜繼昌及院洞任掌田興文(又作全興文)等人,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七月二十八日夜率五十壯士埋伏慶熙宮,姜龍輝和田興文則在姜月惠和姜繼昌的引導下來到正祖的書房尊賢閣,爬上屋頂,伺機刺殺正祖。
正在讀書的正祖發現上面落下瓦礫,便命宦官查看屋頂,姜、田二人逃走。其後正祖移禦昌德宮,田興文于八月十一日試圖再次闖宮行刺,但在西門景秋門牆下被衛兵金春得逮捕,由此牽出了洪啟禧家族一連串逆謀,除了刺殺正祖外,還有詛咒正祖和洪國榮、推戴正祖異母弟恩全君李禶等,是為“丁酉之變”。事後,洪啟禧家族成員被悉數處死。
正祖李祘軍服像(韓國現代畫家李吉範繪)
正祖肅清了反對派、坐穩了王位後,效法英祖頒布《闡義昭鑒》而先後頒布《明義錄》《續明義錄》,宣布鄭厚謙、洪麟漢、洪相範等逆賊罪狀,闡明自己的正統性,并安排洪國榮等為“義理主人”,負責維護自己所确立的《明義錄》義理。其時洪國榮身負保護正祖之任,兼任都承旨和禁衛大将,權勢熏天,有“勢道”之稱。他把妹妹(元嫔洪氏)送入宮中,元嫔不久就死去,洪國榮讓正祖之侄常溪君李湛(恩彥君之子)當元嫔的代奠官,稱“完豐君”,叫他“吾甥”,試圖讓他過繼給元嫔洪氏,成為正祖的儲嗣,又謀害王妃金氏(孝懿王後),正祖發覺後,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九月令洪國榮緻仕,稱“奉朝賀”,翌年二月以接受吏曹判書金鐘秀等人彈劾的形式,将洪國榮逐出朝廷。不過隻是隐晦地談到洪國榮阻止正祖揀擇後宮、妨礙“廣儲嗣之道”,也沒有将洪國榮處以死刑。
驅逐洪國榮以後,正祖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九月終于得子,即宜嫔成氏所生之文孝世子李㬀。然而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五月和九月,文孝世子和宜嫔成氏相繼去世,十一月,常溪君李湛暴死。十二月一日,王大妃金氏(貞純王後)突然出來揭發洪國榮生前想讓常溪君過繼給元嫔洪氏為養子、成為正祖儲嗣的陰謀。十二月五日,常溪君外祖父宋樂休又告發常溪君暴死與前領議政金尚喆、前訓練大将具善複、具以謙父子有關。
其後查明具善複等曾參與害死莊獻世子,擔心正祖報複,便決定勾結常溪君“反正”,推翻正祖。具善複被處死,但不批準處置金尚喆的請求。至此,正祖才将所有反對勢力全部清除。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正祖納樸準源之女為嫔禦(綏嫔樸氏),三年後再次得子,是為後來的朝鮮純祖李玜。嘉慶五年(1800年)正月,正式立李玜為王世子,他還計劃在甲子年(1804年),即李玜十五歲時禅位于他,自己則奉生母惠慶宮洪氏移居新建的水原華城。
抱憾而終
正祖年間,朝廷圍繞“壬午義理”而分化為時派和僻派,但正祖始終能駕馭于兩派之上,因此朝中并沒有明顯的黨争,政局大體保持穩定。正祖一改英祖晚年重用外戚的方針,标榜“右賢左戚”(重用士大夫、排斥外戚),同時繼續執行蕩平政策,并起用失勢已久的南人黨,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禦筆特拜南人蔡濟恭為右議政,翌年正月升任領議政。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月又罷免蔡濟恭,改任老論時派金履素為領議政。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時派“貴近”之臣鄭東浚因胡作非為而被權裕彈劾為契機,正祖又起用俞彥鎬、尹蓍東、沈煥之等僻派。
經過二十餘年的實踐,正祖對士大夫感到失望,認為他們不能抛棄黨争的“俗習”并追随自己的路線(“義理”),這種失望感在嘉慶五年(1800年)五月三十日(晦日)發布的“五晦筵教”中爆發出來。當時,正祖拜出身少論時派的右議政李晚秀為吏曹判書,出身老論時派的弘文館修撰金履載以“相避法”為由提出反對,被正祖罷免,随後正祖在“筵席”上發表長篇大論,借闡明對金履載的處分理由來警告群臣緊跟君主的路線,不得自作“義理”。
與此同時,正祖也在改變“右賢左戚”的做法,摸索以外戚為中心的新的政局運營方式。在冊立李玜為世子後,就開始揀擇世子嫔,正祖看中了老論時派中的金祖淳,準備把他的女兒揀擇為世子嫔,又在六月十四日召見金祖淳于昌慶宮迎春軒,坦承自己二十多年來的“右賢左戚”路線已經破産,囑托金祖淳在自己退位後輔佐新君,以外戚身份主導國政。
就在正祖計劃大幅調整國政運營方式的時候,一向健康的他開始生病并迅速死亡。嘉慶五年(1800年)六月十日,正祖告訴衆大臣,自己身上長出膿瘡,并開始塗藥去膿。之後病情逐漸惡化。六月十四日,醫官開了夾紙膏與杏仁膏,并制作加減逍遙散。但正祖将膿包自行診斷為心裡的火病,并飲用了兩服白虎湯,之後全身開始出現滾熱的症狀。六月十六日,正祖命令呈上四順清涼飲、金蓮茶與五顆牛黃,之後又服用了乳粉托裡散和三仁田螺膏、貝母膏、香薷調中湯。
六月二十五日服用了龍腦安神丸和牛黃清心丸,六月二十六日服用了瓊玉膏、八物湯,吃了五錢人參。六月二十八日服用了三錢人參,之後在昌慶宮迎春軒再次召見金祖淳時,病情突然惡化,以緻說不出話來。此時金大妃(貞純王後)命人送去藿香正氣散,正祖服用後不久就在酉時停止了呼吸,享年四十九歲,沒能等到兌現退位以後和母親在水原華城安享晚年的“甲子之約”的那天。
世子李玜即位後,為其父王上廟号“正宗”,谥号“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大王”(清朝賜谥“恭宣”,朝鮮内部不用),葬于健陵。光武三年(1899年),朝鮮高宗加上尊号“敬天明道洪德顯谟”,随即升格為帝,廟号改為“正祖”,谥号“敬天明道洪德顯谟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宣皇帝”。
為政舉措
政治
峻論蕩平與右賢左戚
正祖與其祖父英祖一樣标榜“蕩平政策”,對朋黨加以平衡與抑制,但不同于英祖的“緩論蕩平”路線,正祖走的是“峻論蕩平”路線,英祖的蕩平政策的核心是“調劑保合”,采取的方法是與老、少論中的“緩論”大臣聯姻并重用這些外戚,排斥以清議标榜的“峻論”士大夫,稱他們為“清名黨”并加以打壓。正祖則反其道而行之,不再一味“調劑保合”,而是強調忠逆、是非、義理的重要性。他上台不久後就鏟除自己的生母家族洪氏、繼祖母家族金氏、表兄家族鄭氏等英祖朝得勢的外戚家族,并重用被英祖貶為“清名黨”的清論士類,這種用人方針被稱為“右賢左戚”,即重用“賢士大夫”,排斥外戚宦官,自稱他治國之道就在于“疏戚裡、抑宦官”六字訣。
其後朝中士大夫分化為時派和僻派,正祖将追随自己的時派引為自己的近臣,對僻派也不予擯斥,使兩派勢力構成平衡。不過,正祖推行了二十多年的“峻論蕩平”路線與“右賢左戚”方針之後,還是發現士大夫難改結黨之弊,各自遵從各自的“義理”,對強化王權構成障礙。因此他又決定重用外戚,挑選時派中的金祖淳與自己聯姻,并委任金祖淳以外戚身份主導朝政,于是在正祖去世後不久,蕩平政治落下帷幕,繼之而起的是外戚專權的“勢道政治”。
設奎章閣與抄啟文臣
正祖繼位不久後,就模仿宋代館閣制度,在昌德宮後苑建立“奎章閣”。奎章閣起初隻是保管國王禦真、禦制的機構。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正祖罷黜洪國榮、正式親政以後,奎章閣作為政治機構的機能不斷提升。他将自己的親信安排到奎章閣任職,使之得以接近君主、參決國政,故奎章閣被稱為“内閣”。同時又先後安排10批、共計100餘名的年輕文官到奎章閣讀書撰文,接受培訓,稱“抄啟文臣”,從而培養了自己的支持勢力。正祖死後,奎章閣的政治機能受到限制,此後基本上隻作為王室圖書館而存在。
君師政治
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以後,正祖不再開經筵,即不再讓儒士教導自己,反而以抄啟文臣這種制度來教導儒士。正祖後期,更是明确标榜自己是集王統和道統于一身的“君師”,即“以君兼師” ,表示自己“在君師之位,任君師之責”。他作為“君師”的職責就是實行“矯俗之政”,具體來說就是矯正士大夫無視君主、結黨營私之弊俗,從而強化王權。不過收效并不理想,因此他在臨終前的“五晦筵教”中對群臣加以警告。
營建華城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祖将位于楊州拜峰麓的莊獻世子墓—永佑園移葬至被稱為“明堂”(風水上佳之地)的水原花山,改稱“顯隆園”。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改水原為華城,升格為留守府(相當于陪都),因花山之“花”與“華”相通,且取華封三祝之典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二月開始在八公山下營建華城(水原新邑),由右議政蔡濟恭負責督建。該城與朝鮮半島其他用花崗岩修築的城池不同,采取中國式磚城的模式,同時使用了出身南人的實學家丁若镛設計的起重機,體現了當時朝鮮的“北學”與“西學”的成果。因此,原計劃十年修好的華城隻用了兩年半時間就竣工,并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在華城行宮舉行了正祖生母惠慶宮洪氏的還甲盛宴。正祖本欲在嘉慶九年(1804年)退位,奉惠慶宮洪氏移居華城,但未能如願。
完善典章
正祖延續英祖朝所推進的整備典章的政策,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将《經國大典》與《續大典》及之後的一些新法規合為《大典通編》。此外還将禮曹所負責的禮儀制度合編為《春官通考》、将對清和對日的外交文書合編為《同文彙考》。
經濟
通共政策
朝鮮王朝奉行“利權在上”、“重農抑商”的政策,自太宗朝以來,商業完全由國家掌控。除了最大的特權官商“六矣廛”外,還有登記在“市案”的“市廛”,承擔“國役”(為國家采購産品),享受着國家賦予的“都賈”(專賣)權。而私自開設的商店則被稱為“亂廛”,如果“亂廛”所涉及的商品觸及六矣廛和其他市廛的壟斷經營權(都賈權),六矣廛和其他市廛可以強制關閉亂廛,是為“禁亂廛權”。正祖年間,領議政蔡濟恭力主“通共和賣”,反對禁亂廛權,正祖采納其建議,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下令廢止三十年來新開的市廛,并取消“六矣廛”外一切市廛的禁亂廛權,是為“辛亥通共”。于是朝鮮王朝堅持近四百年的商業管制大幅放開,私商日益活躍,有力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礦業政策
朝鮮王朝自孝宗以來,實行“設店收稅法”,向民間資本開放礦山采掘。起初該法限定于銀礦和鉛礦,正祖即位後,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開放銅礦,嘉慶三年(1798年)開放金礦,進一步促進礦業的發展。
文化
文體反正
18世紀,中國的稗官小品(野史雜記、明清小說)大量傳入朝鮮,對朝鮮文風産生很大影響。正祖認為稗官小品“最害人心術”,對士大夫沾染這種文風感到憂慮,于是實行了“文體反正”的文化政策,即抑制稗官小品的影響,倡導“正大醇厚”的古文。他一方面對崇尚稗官小品的文臣加以懲戒,如李相璜、金祖淳、南公轍等,迫使他們上疏謝罪,與稗官小品劃清界限,并将“純仿小品體裁”的成均館儒生李钰開除學籍;另一方面,他加大對從中國進口書籍的管控,嚴禁士人閱讀明末清初文集和稗官小說,并焚毀相關書籍。不過該政策效果有限,正祖死後,稗官小品繼續流行于朝鮮。
尊周思明
正祖延續前代國王肅宗、英祖等倡導“尊周思明”的意識形态的政策,強調尊周思明、春秋大義“實為正世道、培國脈之最先務”。他說他在同清朝、日本交往的過程中,都會懷念明朝對朝鮮的恩德。因此,他尤其推崇标榜“尊周思明”的老論大儒宋時烈,稱他為繼承朱熹道統的“宋子”,刊行《宋子大全》,并禦定《兩賢傳心錄》(“兩賢”即朱熹與宋時烈)。他還非常注重“尊周思明”相關書籍的編纂,親自主持對《宋史》的修訂,修成《宋史筌》,以體現尊周大義,同時編纂了《尊周錄》《尊周彙編》《皇明時槐院謄錄》《明陪臣考》《皇明陪臣傳》《斯文大義錄》《明紀提挈》等大量“尊周思明”的相關書籍。
對天主教
正祖年間,天主教已經傳入朝鮮,并發生了一系列逮捕天主教徒的案件,如乙巳秋曹摘發事件、丁未泮會事件、辛亥珍山事件等。正祖雖視天主教為“邪教”,但始終沒有展開大規模搜捕與鎮壓天主教的行動,他反複強調“正學明則邪說息”,認為“予意則使吾道大明,正學丕闡,則如此邪說可以自起自滅”,他把天主教看作是陸王心學、佛教道教一類,認為無需厲行禁止,隻要儒生熟讀儒家經典、不看雜書,便可迎刃而解。所以,盡管當時不斷有大臣上疏請求鎮壓天主教,正祖卻不予受理,隻在告發的情況下加以懲治,并盡量避免事态擴大化,特别是蔡濟恭出身南人,更是對多為南人的天主教徒曲加庇護,并未演變為大規模的鎮壓行動,天主教也在朝鮮方興未艾。
據天主教徒黃嗣永所說,正祖雖然不喜天主教,但考慮到主持朝鮮教務的周文谟神父(司铎)是中國人,涉及到與清朝的關系,如果公開抓捕,處置就極為棘手,因此禁教都是暗中進行,同時派人裝成天主教徒,潛伏在教會裡,以便找到周文谟的行蹤并将他暗殺,但這個計劃還沒成功就去世了。正祖去世後,貞純王後發動“辛酉邪獄”,這是朝鮮第一次對天主教的鎮壓。
社會
親民政策
正祖在朝鮮王朝曆代君主中以親民著稱。他頻繁出宮,以巡幸京畿道一帶的各個陵園為名探訪民間疾苦,在位24年間出宮巡幸75次,頻度居朝鮮國王之最,相比之下,祖父英祖在位52年間出宮55次。同時,他還改革訴冤制度,此前百姓直接向國王訴冤被局限于“四件事”(刑戮及于自身之事、明父子關系之事、分揀嫡妾之事、分揀良賤之事),正祖取消限制,接受百姓一切訴冤。據記載,正祖年間收到百姓上言(陳書訴冤)與擊铮(敲鑼訴冤)3217次,其中2671件被受理。
庶孽通清
正祖進一步擴大英祖年間對庶孽禁锢法的松動舉措,即“庶孽通清”。他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出台《丁酉節目》,對“通清”範圍加以規定。正祖還任命了樸齊家、柳得恭、李德懋等庶孽出身的學者為奎章閣檢書官。
廢奴構想
正祖對于朝鮮王朝的奴婢制度非常反感,認為“天下之冤,莫切于奴婢”,是極不人道的制度。他曾構想“一掃奴婢之規,創行傭雇之法”,決定親自策劃廢除奴婢制度,不過很快就去世了。死後,純祖僅廢除公奴婢,保留私奴婢,直到近百年後的甲午更張才徹底廢除奴婢制度。
軍事
設壯勇營
正祖即位時,朝鮮中央軍(五軍營)中外戚勢力很大。正祖為了培養忠于自己的軍隊,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慶祝思悼世子改谥莊獻世子的武科中選拔2000人,作為自己的親衛部隊,不久稱“壯勇衛”。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擴展到20000人的規模,遂改稱“壯勇營”。此後又在華城設置“壯勇外營”。正祖死後,壯勇營被解散。
刊行兵書
正祖繼承生父莊獻世子之遺志,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完成了生父未能完成的兵書,并以《武藝圖譜通志》之名刊行,此外還刊行了《兵學通》等六種兵書。
外交
對清朝
正祖表面上仍強調尊周思明、春秋大義,但他的反清意識已明顯不如之前的孝宗、肅宗、英祖等國王。這從他對乾隆皇帝的評價就可以看出,他認為乾隆帝“自是一代英雄” ,說他“比康熙尤盛焉”,不吝贊美之詞。乾隆帝退位之際,正祖表示:“即使是交友之道,六十年的老朋友突然告别了,仍然有種失落感,何況乾隆對于中國呢?他在位六十年,依然不怠政,如今又親自傳位于兒子,并自尊為太上皇,這是曆代都沒有的盛舉啊!”
除了對清朝最高統治者乾隆帝的贊賞之外,正祖也認識到清朝經濟、文化的高度繁榮和朝鮮的相對落後。他對清朝的先進文化和技術抱有開放、接納的态度。正祖的态度也得到部分知識分子的支持。當時一些朝鮮知識分子以“燕行使”的身份前往北京,目睹清朝保留了先進的華夏文明,而不是什麼蠻夷做派,開始主張吸收學習清朝文化和制度。這種主張向清朝學習的思潮或流派都被叫做“北學”或“北學派”,代表者有樸趾源、樸齊家、洪大容、洪良浩等。
正祖年間金弘道所繪《燕行圖》中的北京朝陽門
正祖時期,朝鮮使行人員回國後所寫的報告——“使臣别單”和“譯官手本”中,不再有“清朝出現危亡之兆”等危言聳聽的字句,即使清朝有白蓮教起義、西征、南征之事,或貪官腐敗等内政弊端,他們也都可以客觀描述。這表明朝鮮開始以平和的心态和客觀的态度看待清朝。正祖也不像前代國王那樣翹首盼望滿清崩潰、中華複興,他關心的是清朝的城郭濠池、市肆、漕運制度,以及《四庫全書》等文化編纂事業。而他最關心的是“利用厚生”之制,即如何利用技術,使民衆富裕起來。“北學派”代表人物洪良浩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從北京回國後,告訴正祖北京和沈陽一帶使用水車灌溉的情況。正祖當即命令工匠造出10輛,分送朝鮮各地推行。不久洪良浩再次上書,系統介紹了清朝的車制、磚窯燒制、驢羊畜牧等,正祖也都悉心學習。正祖所興建的水原華城,也吸收了北學派的主張采用了中國先進的築城方法。
正祖對清朝的事大禮節也盡心盡意。他曾親自動手檢查使行的貢包,查看貢品有無質量問題。由于對清朝的戒心逐漸放松,向來被朝鮮視為邊防重地、與清朝接壤的地方,在正祖時期也得到了開發。如一直作為天險處于未開發狀态的“廢四郡”地區(鴨綠江上遊邊境),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開始允許百姓開墾入住。乾隆帝也認為“于屬國中最稱恭順”,他對朝鮮厚加賞賜,曾親自召見朝鮮使臣,賜酒吟詩,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親書“東藩繩美”四字匾額,送給朝鮮,并給正祖寫“福”字,祝福其早得貴子。總之,正祖時期的朝鮮與清朝的關系不僅更加融洽,也是朝鮮統治者克服對清敵意和危機意識,開始正視清朝、吸收清朝文化的時期。
在朝鮮的對清貿易方面,正祖年間也出現重大轉機。英祖時,因對清貿易的嚴重逆差,曾出台“禁紋令”,即禁止從清朝輸入有花紋之綢緞。正祖繼位後堅持這樣政策,并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重申《禁紋節目》,并鼓勵“鄉織”(朝鮮本土紡織)。然而正祖年間,朝鮮人工栽培人參(紅參)的技術日益成熟,無須依賴在中朝邊境采集野生人參,故正祖松弛百年之久的禁參政策,于嘉慶二年(1797年)允許燕行使譯官攜紅參出境交易,從此朝鮮對清貿易複振。
對日本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日本江戶幕府第10代征夷大将軍德川家治去世,養子德川家齊襲位。按慣例應由日本對馬藩邀請朝鮮通信使,但此時的日本國力衰落,連逢天災,尤其是“天明饑馑”導緻社會動蕩,财政困難,無法接待通信使,而且讓朝鮮通信使看到日本饑荒的慘狀也有損“禦威光”(将軍的體統),故幕府老中松平定信指示對馬藩延期邀請通信使,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江戶幕府又提出“易地通信”,即通信使交聘地點不在江戶而在對馬島,朝鮮方面以違背前例為由未予接受。直到正祖死後的嘉慶十六年(1811年),朝鮮才接受日本“易地通信”的要求,向對馬島派出了最後一次通信使。
曆史評價
自評:①涵養工夫最難,餘少涵養工夫,故每多暴發之病。②予豈有學問工夫?而特以經曆之多艱,自不能無動心忍性之工矣。
朝鮮王朝官方評價:王緻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道學之正也;建天地而不悖,俟百世而不惑,義理之正也;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而萬民萬事無不正,治法征谟之正也。精一之傳,祗承于聖祖;燕翼之谟,付畀于聖子。成始成終,王者之大居正也。傳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王之所以為正也。……王以孔、朱之學,任堯、舜之道,大啟斯文,以應五百命世之作,而斯民無祿,天啬其壽,聖聖相傳之統,遂不可複徵。子曰:“道之不行也,學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蓋亦氣數之使然欤?嗚呼痛矣!(李晚秀撰正宗大王行狀)
乾隆帝:該國王如此遇事知儆,益見其恭順自将,足以永受恩眷,深為該國慶幸也。
朝鮮高宗:至我正廟,以天縱之聖,懋日新之工,發揮斯文,崇獎儒學,鼓舞一世,而跻之文明之域,巍巍乎其功也,郁郁乎其文也。敬讀雅誦序文,則聖祖之允承朱子之統有不可誣矣。
林泰輔(日本學者):英祖、正祖二君,于李朝曆代中,實可謂出類拔萃者。不幸承黨争之後,其餘弊不易掃蕩。雖勞心苦志,收效甚微。然有一層之進步,則可無疑也。
李丙焘:王且為好學能文之主,富于著作,遺有巨帙文集《弘齋全書》。王在文章與經學方面,主張純粹性與正統性,如同其廟号所示,确為維持正宗之主。
李泰鎮(韓國學者):正祖的政治思想一言以蔽之可以命名為“聖君絕對主義”。這與幾乎同一時期歐洲的啟蒙絕對君主的思想多有類似之處。據悉,啟蒙絕對君主們堅持着自我智慧探究,樹立自己應成為國内最健全、最出色的人的指标,并欲以此成為行使政治絕對權的根據。正祖所追求的也是要成為國内最健全的人。而且啟蒙絕對君主為了确保這種主張的客觀性而追求法治,正祖在這點同樣是絲毫不亞于他們。可以認為,即使稱正祖為“儒教的啟蒙絕對君主”也是毫不遜色的。伏爾泰曾給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說清朝的乾隆帝是啟蒙君主的典型,但正祖在儒教帝王學的實踐層面一點也不比乾隆帝差。
鄭玉子(韓國學者):朝鮮采用性理學理念,标榜“右文政治”,400年後誕生了名副其實的典型的學者君主。……因為有深厚的學問基礎,他可以自居“君師”,領導臣子。在崇尚學問的時代,他以卓越的學術能力确保了“君師”的地位,從而統治一個文化國家。
人際關系
關系 | 稱号 | 姓名 | 備注 | |
父母 | 生父 | 思悼世子 | 李愃 | 李祘改谥莊獻世子,朝鮮高宗追尊莊宗大王,旋升為莊祖懿皇帝 |
生母 | 惠慶宮 | 洪氏 | 初谥獻敬惠嫔,朝鮮高宗追尊獻敬王後,旋升為獻敬懿皇後 | |
養父 | 孝章世子 | 李緈 | 朝鮮純宗追尊真宗昭皇帝 | |
養母 | 孝純王後 | 趙氏 | 朝鮮純宗追尊孝純昭皇後 |
轶事典故
雅号由來
正祖主要有兩個雅号,一個是他早年所取的“弘齋”,取自“君子弘毅”之義;又全稱“弘于一人齋”,取自中國上古時期《卿雲歌》中“日月光華,弘于一人”。另一個是“萬川明月主人翁”,這是他晚年的自号。他把臣民比作河川,自己比作映照“萬川”的“明月”,并融合太極思想,将他的政治哲學用《萬川明月主人翁自序》這篇文章來加以闡釋。
嗜書之癖
正祖在朝鮮王朝曆代國王中以嗜書著稱。他還是世孫時,就熱衷藏書,聽說在中國購買的書和家藏秘本,就馬上下令買來,收藏在“皆有窩”中,經史子集無所不有,并讀遍這些書籍。而且他還給自己安排讀書計劃,除非生病,否則必須按計劃完成,即位以後也保持這種習慣,有時在晚上接見大臣結束後,往往會秉燭讀書,完成計劃後才能安心睡覺。同時,也勤于做讀書筆記,分類輯冊,以便記憶。
正祖即位後,雖然政務繁忙,但仍然以“靜坐一小窩對方冊”為樂。最讓他愉快的事就是在處理完政務後與幾個文人學士“談經說詩,讨古證今”。正祖最愛讀的書是《宋史》,從早年開始就每年看一遍,反複披閱,多年不倦,原因在于他認為朝鮮王朝的制度最像中國宋朝,所以研究《宋史》有益于治國理政。此外他時常将明人丘濬《大學衍義補》和《王陽明集》放在桌案上,每年都會閱讀,他對王陽明的文章尤其推崇,對歸有光、張居正也予以肯定。但總體而言,正祖對明清人的文章評價不高,認為“多險怪尖酸”,對稗官小說尤其深惡痛絕,自幼不看一眼。
開同德會
乾隆四十年(1775年)十二月初三日,因洪國榮所物色的行副司直徐命善上疏彈劾洪麟漢,使還是世孫的正祖得以擺脫危機,實現代理聽政,故這個日子被正祖定為紀念日。正祖沒有選擇像過去的君主那樣策勳功臣,而是在每年十二月初三日召集當初保護自己的人召開名為“同德會”的聚會。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二月初三日,正祖召見已被提拔為右議政的徐命善及自己曾經的僚屬洪國榮、鄭民始、李鎮衡,召開第一次同德會,在正祖發表講話後,一起祭拜神殿,然後舉行小型宴會,正祖禦制《同德會軸序》,其他與會者也寫了文章。此後大多數年份的十二月初三日都會開同德會,直到正祖去世。
擅長射箭
正祖允文允武,不僅以學識淵博著稱,也擅長武藝,尤其是射箭,堪比朝鮮太祖。每次射十巡(每巡五次),他都會連中四十九次,最後一次則不射,以表現謙遜的美德。還有一次,他将棍杖放在百步開外的地方,五發五中,又将折疊小扇放在百步開外的地方,也是沒有一次不中的,被稱為“神弓”。一些号稱善射的大臣如尹行恁、李益運、嚴耆,其射藝都無法跟正祖相提并論。
乾隆賜福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正月十一日,乾隆帝在圓明園接見朝鮮冬至使李性源一行,詢問正祖有無男嗣,李性源回答:“一國臣民正在盼望呢!”兩天後,乾隆帝再次召見李性源等,拿出兩個漆盒,說裡面裝着他為正祖寫的“福”字,以此祝福正祖早得貴子,此外還有玉如意、福字方箋等禮品。朝鮮使臣将乾隆禦筆“福”字帶回國後,正祖将此字出示給大臣們看,左議政蔡濟恭、右議政金鐘秀紛紛稱贊乾隆帝“筆力極其雄豪”“筆力如是雄健”,并表示這是曠古恩典,感謝乾隆帝賜“福”字。
正祖也很高興,稱贊“筆力異于凡常”,并說:“清朝皇帝對待我,超出常規。他手書福字,在萬裡之外祝福我,這份心意難道不很讓人感到很厚重嗎?我對他也不能不更加深情厚意。這并不違背尊周大義。”乃命詞臣作《謝賜筆表》,交乾隆帝八旬大壽進賀使黃仁點一行呈給清廷。乾隆帝賜“福”字時,綏嫔樸氏已經懷孕,當年六月十八日生下元子(後來的純祖),七月,在承德祝賀乾隆帝八十大壽的黃仁點等将這一消息禀告乾隆帝,乾隆帝龍顔大悅,連說:“是誠大喜的事!是誠大喜的事!”
主要作品
正祖是朝鮮王朝曆代君主中留下詩文最多的一位。他留下438首詩、4首樂章、1首訓詞、1258篇文章。他的詩文及一些相關資料被合編為《弘齋全書》184卷100冊(包括他在世孫時期的作品《春邸錄》4卷),這也是現存的第一部朝鮮君主個人文集。
除此之外,正祖在書畫方面也頗有成就,有《芭蕉圖》《墨梅圖》《墨菊圖》《秋風鳴雁圖》《四君子》等畫作傳世,其畫風頗有文人氣息。
朝鮮正祖部分書畫作品
死因争議
有觀點認為,正祖死于老論僻派沈煥之等的毒殺。正祖在嘉慶五年(1800年)五月三十日發表了旨在強化王權、警告臣僚的“五晦筵教”。時為左議政的沈煥之對此感到害怕,便收買醫官沈鏔下毒暗殺正祖。這種說法尤其在受到正祖提拔的南人内部非常盛行,曾有人因散布這種傳聞而被治罪。
不過,随着2009年正祖與沈煥之君臣間299件書劄的公開,沈煥之毒殺正祖的說法逐漸受到史學界否定。檀國大學教授金文植表示:“正祖末年,正祖通過信件向沈煥之告知了自己的病情。如果他懷疑沈煥之,絕對不會向他表明病情。根據信件内容推測,自然病死的可能性更高一些。”
後世紀念
健陵
正祖死後,按其生前遺願埋葬于莊獻世子之墓顯隆園東側,陵号“健陵”,位于今韓國京畿道華城市安甯洞顯隆園講武堂。21年後,孝懿王後去世,與正祖合葬于健陵。同時因風水問題,健陵位置也稍作移動至水原舊邑的鄉校舊址(仍在顯隆園即隆陵範圍内)
遊行活動
自1996年開始,韓國京畿道水原市于每年10月舉行“正祖大王陵幸班次共同再現”活動(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推遲至2021年4月舉行),作為水原華城文化節的一部分。從2016年到2018年,首爾特别市、華城市、京畿道等地方自治團體相繼參與,完整重現了正祖當年從昌德宮到華城及隆陵的“陵幸”隊伍,是韓國最大的王室遊行,也成為韓國地方自治團體聯合慶典的成功案例。屆時,将從市民中選拔正祖和惠慶宮等主角角色,并在昌德宮、舟橋、鹭得島、水原華城、隆陵等沿途主要景點舉行舟橋市民體驗、美食集市、正祖大王主題展覽館、傳統文化表演等豐富多彩的市民參與活動。
遊行活動
影視形象
類型 | 名稱 | 年代 | 飾演者 |
電影 | 望夫石 | 1963 | 金雲夏 |
十年勢道 | 1964 | 李秀練 | |
浸透淚水的王冠 | 1965 | 李承宇 | |
永遠的帝國 | 1995 | 安聖基 |
參考資料
1.正祖禦真 ·禦真博物館
2.《朝鮮王朝實錄·正祖實錄》附錄,惠慶宮書下行錄·國史編纂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