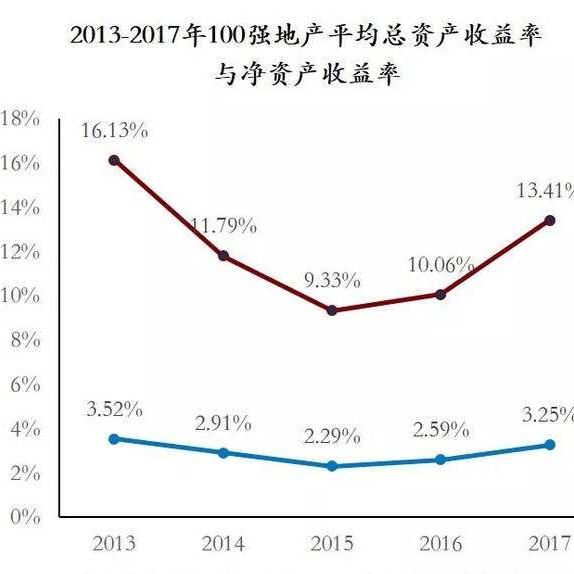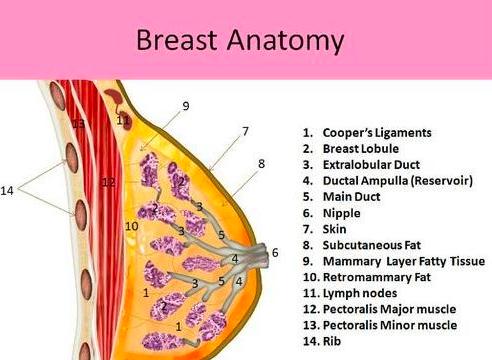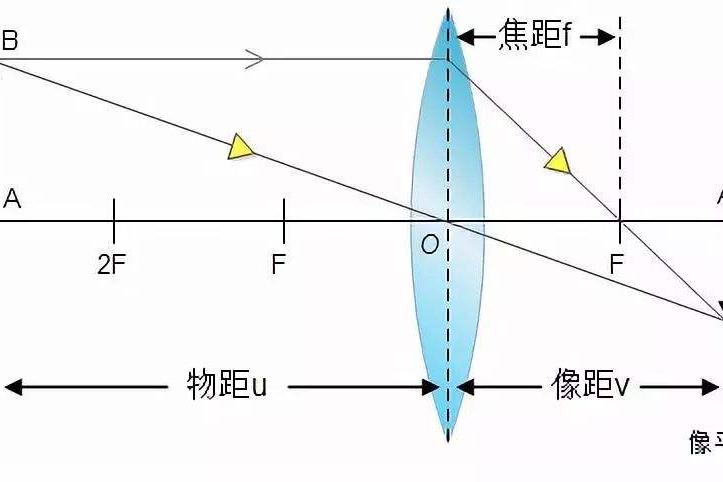基本分类
国际制裁一般包括外交制裁、经济制裁和军事制裁等。
外交制裁,通常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外交领域采取主动行动,对另外一个国家予以惩处,以维护本国的尊严,或者公开表示本国政府的愤怒与不满。外交制裁是一种国家行为,仅限于外交领域,其做法须是和平、非暴力、约定俗成的,通常在外交交涉失败后采用这种方式。比较常见的方式有召回大使、断绝外交关系等。
经济制裁是指采用断绝外交关系以外的非武力强制性措施。一般认为,财政、金融、贸易、海运、航空,甚至军火贸易等领域的制裁均属于经济制裁。常见的方式有:贸易禁运、中断经济合作、切断经济或技术援助等。
军事制裁常见的方式包括军事封锁、武力打击、摧毁设施等。
外交制裁和经济制裁均属非武力制裁。联合国对伊拉克、前南斯拉夫、利比亚、海地、利比里亚、卢旺达、索马里、安哥拉反政府武装(安盟部队)、塞拉利昂、阿富汗及埃塞俄比亚等国进行了强制性制裁。
国际法上的制裁有单独的和集体的两种。单独制裁是由个别国家,主要是受害国,对违反国际法的国家施加有形的或无形的压力,迫使它停止其不法行为,或为其不法行为承担后果。单独制裁在很大程度上和国际争端的强制解决的方法是一致的,如报复、报仇、平时封锁,以及自卫(包括集体自卫)等自助行为。单独制裁可以是在道义、政治和舆论方面,如对不法行为进行揭露、谴责;可以是在外交方面,如断绝外交关系;可以是在经济方面,如对不法行为国实行禁运、抵货;也可以是在军事方面,如进行武力自卫反击。
单独制裁
国际制裁是指对作不法行为的国家的制裁,不包括对个人的制裁。个人作了国际法(包括条约)所禁止的行为,虽然也要受到惩罚,但这种惩罚是各个国家根据国际法或条约被授权或承担义务所施加的,如对海盗、妇女贩卖者、毒品贩卖者、飞机劫持者,以及战争罪犯的制裁。当然在某些情形下,对个人制裁也实际上起对国家制裁的作用,如对战犯的制裁。
集体制裁
集体制裁是国际社会对违反国际法行为的有组织的强制行动。集体制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形成的制度。依照1919年《国际联盟盟约》第16条,国际联盟会员国如果不顾盟约第12条、第13条或第15条的规定而从事战争,应视为对联盟所有其他会员国的战争行为并应予以制裁。其他会员国应即与之断绝各种商业上或财政上的关系,禁止其人民与破坏盟约国人民的一切交往,并阻止其他国家人民与该国人民间的上述交往。如果这些措施未能迫使违反盟约的国家放弃其违反盟约行为,国联行政院应向会员国建议派遣和组织军队以维护盟约。遇有此种情形,经出席行政院所有会员国(违反盟约的国家除外)的投票表决,可将违反盟约的会员开除出盟。尽管有上述规定,在国联历史上这种制裁并未真正付诸实施。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侵华战争,国联行政院于1932年派遣调查团到中国进行调查,国联大会于1933年2月24日全体一致(当事国一方日本除外)通过了调查团报告书。尽管该报告书多方迁就日本侵略、损害中国主权,日本仍悍然拒绝接受,并退出国联,而且更加疯狂地扩大对华侵略。国联未能进行一步对日本采取有效的集体制裁。1935年意大利法西斯侵略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由于英、法的纵容,虽然国联行政院决定对意实行经济制裁,但未认真执行。1936年意大利公然吞并阿比西尼亚,国联大会竟在英、法建议下撤销对意制裁。
相关规定
1945年《联合国宪章》对于威胁和平、破坏和平及侵略行为的制裁问题,在第7章中作了明确的规定:安全理事会应首先“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之是否存在”(第39条),并提出临时办法,要求会员国“遵行”(第40条)。它得“决定”采取武力以外的办法,如经济关系、铁道、海运、航空、邮电、无线电及其他交通工具的局部或全部停止,以及外交关系的断绝,以实施其决议,并得促请会员国执行此项办法(第41条)。安理会如认为上述办法还不够时,得根据第42条规定,采取必要的空海陆军行为,包括会员国的空海陆军的示威、封锁及其他军事举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
遇此情况,会员国应依特别协定供给必要的军队、协助及便利,包括过境权。安理会关于国际部队之使用及统率问题由军事参谋团予以协助,军事参谋团由各常任理事国的参谋总长或其代表组成。根据第25条,安理会的决议对会员国有拘束力,会员国同意接受并履行安理会的决议。对于安理会在宪章第7章下有关执行行动的决议,常任理事国,即令是事端当事国,也可以行使否决权。
联合国大会具有广泛职权,它可以讨论宪章范围内任何问题,并向会员国或安理会,或兼向两者,提出建议(第10条),这当然包括关于制裁侵略的建议。宪章第12条规定,联大的权力限于建议,无拘束力,而且对于安理全正在受理的问题,非经安理会请求,联大不得提出任何建议。1950年,在美国侵略朝鲜期间,美国利用它在联大中控制的多数,于11月3日强行通过所谓“联合一致、共策和平”的决议,不顾宪章第12条的规定及第24条关于安理会对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规定,授予联大使用武装力量“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权力。决议还规定经安理会任何7个理事国的要求,而不是包括所有常任理事国在内的7个理事国的要求,应召开联大特别会议以决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措施。联大并得设立和平观察委员会、集体办法委员会,并利用联大的临时委员会(Interim Committee)在联大闭会期间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这些规定当时都是违反宪章,使联大篡夺安理会职权的非法规定。但国际情况在改变,70年代以来,有不少国家提出加强联合国、扩大联大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职能的主张,这个问题正在探索和讨论中。
联合国自1945年建立以来,在其制裁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及侵略行为方面的实际表现是:1950年,对美国侵略朝鲜不但没有加以制裁,反而允许其假借联合国名义,为其侵略行为披上合法外衣。以后其他重大的侵略行为,如1978年越南侵略柬埔寨和占据老挝,1979年苏联侵略阿富汙,以及以色列多次侵略阿拉伯国家,南非多次侵略非洲邻国,虽然在联合国大会上受到了一定的道义上的谴责,但都没有受到联合国的坚决和有效的制裁。
反外国制裁法出台,表明我国越来越善于运用国际规则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国际规则是国际社会共同制定、遵守的规则,尤其是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代表的全球性国际组织的章程、在实践中形成的规则,也包括国家之间缔结的双边条约。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家间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国际规则对国际关系的建构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国际规则不仅左右国家间利益分配,而且决定一国在国际社会所能扮演的角色,并对其国际行为合法性进行评判,国际规则话语权之争已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重要形式。”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张晓涛举例说,为落实联合国气候框架变化公约而召开的世界气候变化大会,要达成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应对气候变暖的减排协定,中间经历了京都议定书、巴厘路线图、哥本哈根协议等多次讨论,旷日持久,直至达成巴黎协定。这其中最大的争议,就在于在能源使用与碳减排上应确立什么样的国际规则。
近百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经历了从“被动融入”到“主动塑造”的过程。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在国际社会没有话语权。改革开放后,中国选择融入国际社会,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由于多数国际规则的制定已经由西方国家主导完成,作为后来者的中国往往要通过对既有国际规则的认同来参与国际治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国际制度的创建和国际规则的制定上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
进入新时代,中国积极运用国际规则、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设立及正常运营,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肯定;“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大多数国家积极响应;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中国与其他国家一起引领国际规则制定,使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成为巴黎协定达成的重要一环,在推动净零排放等方面正在发挥重要作用。
“反外国制裁法既总结我国反制实践和相关工作做法,又梳理国外有关立法情况,还充分考虑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李庆明认为,反外国制裁法的出台表明,我国越来越善于运用国际规则开展斗争。
今天的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是国际舞台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国际规则直接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影响到中国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我们要做和正在做的,就是学会如何最大限度地运用现行规则、如何在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最大可能保护自己的利益。
“既要看到我们在国际规则话语权上的不足,也要看到我国国际规则话语权不断增强的态势。”李庆明指出,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国际规则各不相同。有的领域国际规则相当成熟,改进空间小,有的领域还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稳定的国际规则,有些国际规则影响全局,有些则局限于较小范围。要增强中国的国际规则话语权,必须抓住重点领域。对于一些不公平的国际规则,要在适当时机争取修订。对于一些新的国际规则的创建,要体现中国思想、中国价值和中国方案。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国际规则更加民主化、自由化、法治化。
加强国际规则运用,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深入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和追逃追赃
李华波,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红色通缉令”2号嫌犯,涉嫌贪污公款9400万元,2011年1月潜逃至新加坡。案发后,国内多部门启动追逃追赃工作,组成工作组先后8次赴新加坡与新方执法部门进行磋商。中新两国在没有缔结引渡条约的情况下,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开展追逃追赃合作。中方向新方提出司法协助请求,提供有力证据;新方冻结了李华波涉案资产,依法对李逮捕、起诉,以“不诚实接受偷窃财产罪”判处其15个月有期徒刑,并在李华波出狱当天将其遣返回国。
积极利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双边条约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是我国利用国际规则开展反腐败斗争的生动例证。中国是最早签署和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国家之一,坚定支持《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全球反腐败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2006年,我国向联合国声明将《公约》视为开展引渡合作的法律依据,并指定司法协助中央机关,多次在相关场合强调希望与各缔约国,特别是尚未缔结双边条约的国家开展合作。在李华波案中,我国和新加坡在《公约》框架下进行了良好合作,追回腐败赃款2700万元。
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成为首个由我国主导制订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文件;2016年9月,中国推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通过《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开创性地提出对外逃腐败人员和外流腐败资产“零容忍”、国际反腐败追逃追赃体系和机制“零漏洞”、各国开展反腐败追逃追赃合作时“零障碍”的概念,这是继《北京反腐败宣言》之后,在多边框架下再一次以国际文件的形式明确提出加强国际反腐务实合作的“中国主张”。2019年4月,我国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发起了《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廉洁建设。2020年12月,国家监委召开“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廉洁建设研讨会,会上中方坚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呼吁加强疫情防控领域反腐败合作,赢得与会代表的普遍赞誉。我国还加强与国际刑警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务实合作,不断健全多边合作机制。
与此同时,我国深入研究域外法律和国际规则,与多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司法协助条约、资产返还与分享协定等,积极开展对外执法合作,综合运用引渡、遣返、境外缉捕、异地追诉等法律手段,追回了一批外逃多年、涉案金额巨大的腐败分子。“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外逃13年,先后窜逃至6国1地并3次申请政治避难,我方与多个国家开展合作,使其最终成为“无处可逃”“无钱可花”“无人可靠”的“三无”人员,被迫回国投案。
6月2日至4日,“预防和打击腐败的挑战和举措,加强国际合作”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以线上线下混合方式召开,中方就反腐败国际合作提出“四个坚持”的政治主张,得到与会者高度赞扬和认同。中国积极参与反腐败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将“中国经验”“中国主张”写入本次特别联大政治宣言,为反腐败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人员往来、信息交流频繁密切,任何国家想关起门来反腐败,既不现实,也不会彻底。”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强对国际规则的运用,依规依法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对内凝聚党心民心,对外占据道义制高点,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