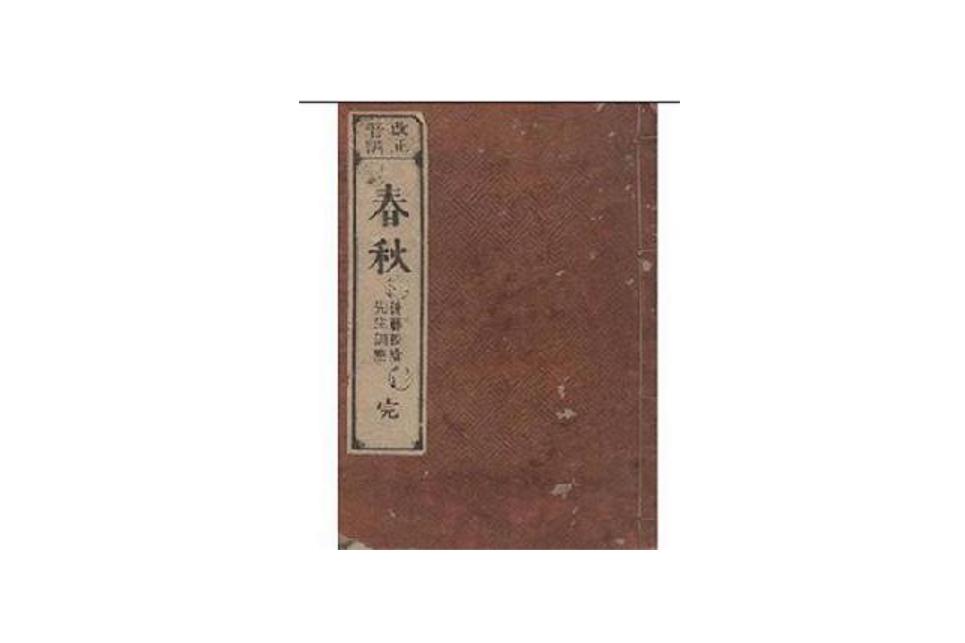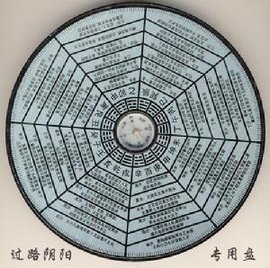实例
记言叙事文之祖:
我国散文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殷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占卜后把占卜日期、占卜人,所占之事,有的还包括日后吉凶应验情况,刻在甲骨之卜兆旁,此即甲骨卜辞。甲骨文清末发现于河南安阳,是商王盘庚迁殷后至殷亡时的遗物,距今已三千多年。这些卜辞所记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祭祀、农业生产、田猎、风雨、战争、疾病等许多方面,真实朴素地反映了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状况。甲骨卜辞记事比较简单,不成系统,但未经后人加工,保持了商代记事文字的原貌。这些占卜之辞,短的只有几字,长的有百余字,比较完整的
这条卜辞,时、地、人、事齐全,叙述较为详细,略具叙事要素。这些卜辞,可看作是先秦叙事散文的萌芽。
同样未经后人加工的商周铜器铭文,反映了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至繁的发展。商周时君王、公侯、臣子都可作铜器铭文,君王所作铜器被视为国之重宝。铜器铭文有长有短,广泛记述了社会生活。商代铭文记事简单,形式一律。如:“丁巳,王省夔京,王易小臣俞夔贝,惟王来征夷方,唯王十祀有五,肜日。”(《殷文存》上二六·后)开头交代事件发生的时间,然后叙事,内容大多是殷王的赏赐,最后还有告于先祖的祭日,周代铭文字数增加了,内容复杂了。不仅有记事文字,还出现了与《尚书》诰命类似的记言文字。
例如,以记事为主的《曶鼎》,先写了周王策命曶继承父业为王卜者;又写了曶用匹马束丝购买五个奴隶,引起纠纷,曶胜诉之事;还记载了匡季带其奴仆抢劫了曶的十秭禾,曶向东宫控告匡季而胜诉,得到了加倍赔偿的事。叙事已有一定规模了。而像《毛公鼎》等侧重记言的铭文,其中的训诰,已和《尚书》没有什么区别。
尚书
《尚书》在时间跨度上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尚书》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虞书·尧典》等记载了尧、舜、禹等人的传说,是后人的追述,不是当时人的记录。《商书·盘庚》是可靠的殷代作品,也是我国记言文之祖。《盘庚》记录了盘庚要迁都于殷,世族百姓普遍反对,他为说服众人而发表的训辞,古朴艰涩,语言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和形象性。
“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比喻生动贴切,至今仍活在我们的语言中。《周书》主要是诰与誓两种文体,记周公言论最多,《洛诰》、《无逸》、《立政》是告诫成王之言,《大诰》是对诸侯的训令,《多土》、《多方》是对殷民的训诫,《康诰》教训康叔如何治理殷民,《君奭》是周公与召公的谈话。周公的这些谈话和训令,反映了周公的心态,周人的政治思想和周初的社会关系。《周书》的《金縢》和《顾命》以记事为主,《金縢》写武王克商后患病,周公
向先王祷告,愿代武王死,武王病愈。后成王嗣位,周公摄政,武王之弟管叔等散布流言诽谤周公,并煽动殷遗民叛乱。周公率兵平定叛乱,成王心中对周公仍有疑忌,周公避居。于是“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为功,代武王之说。”成王大为感动,亲自迎接周公回朝。这些情节颇曲折而具传奇色彩。《顾命》写成王之死,康王之立,事件的过程和宏大的场面铺叙得很清楚。《尚书》文字古奥典雅,语言技巧超过了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而且这些文诰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响。
春秋
春秋时期经过孔子编定的《春秋》,记事系统,具有自觉的记事意识和写作义例。《春秋》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的通称,后特指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它记载了自鲁哀公元年至鲁哀
公十四年(前722-前481)的历史,对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简洁的大纲式的叙述。《春秋》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具备了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但其记事都很简略,长的不过四十多字,短的仅有一字。因此,其记事虽简而有法,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散文。如隐公元年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有,但事件的因果、过程,人物的行为、性格,都无从知道,仿佛一则新闻标题,而不像一篇文章。
《春秋》是“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维护周礼,反对僭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是其主要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在行文中不是议论性文辞,而是在史事的简略记述排比中表现出来。《春秋》还以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词中表现出作者的爱憎。比如杀有罪为“诛”,杀无罪为“杀”,下杀上曰“弑”等。这种史着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为后代史传文学所继承。
左传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左传》为传述《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后人对此颇多疑义。《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722),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468),基本与《春秋》重合,还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今人一般认为此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最后编定者是一位儒家学者。
与《春秋》一样,《左传》不只是对历史事件作客观的罗列,而且还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作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左传》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同时,作者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公室的卑弱和大夫兼并,表现了新旧政治势力的消长,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
书中还揭露了暴虐昏庸、贪婪荒淫之辈,肯定赞扬了忠良正直之士,尤其是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更反映了《左传》进步的历史观。在《左传》作者看来,有德才能为天所佑;得民或失民,被有识之士当做取国或灭国的重要条件;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人的地位提高了;在君与民的关系中,民的地位提高了。
《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但倒叙与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倒叙就是在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如“宣公三年”先记载了郑穆公兰之死。然后再回顾了他的出生和命名;其母梦见天使与之兰,怀孕而生穆公,故名之兰。《左传》中还有插叙和补叙,性质作用与倒叙类似。这些叙述,常用一个“初”字领起。
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结果,如秦晋崤之战中蹇叔在秦出师伐郑时,已预知了必然失败的结果:“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僖公三十二年)秦师经过周都洛阳北门,王孙满又预言:“秦师轻而无礼,必败。”(僖公三十三年)《左传》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视角广阔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个别段落中,作者也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场景。如写鄢陵之战“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师”中阵地的情况,完全是通过楚子和伯州犁的对话展示出来的。(成公十六年)
《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左传》的战争描写,全面反映了《左传》的叙事特点。《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安革}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不计其数的小战役也写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动。一般说来,《左传》写战争,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
如“僖公二十八年”写城濮之战,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而在行文中,又不断展示晋胜楚败的原因: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军纪,遵守诺言,倾听臣下意见,上下齐心协力。而楚方而是君臣意见分歧,主帅子玉恃兵而骄,一意孤行,盲目进逼晋师。城濮之战的结果也写得很全面,不仅写了晋师大胜,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而且还写了战争的余波:楚子玉战败羞愧自杀,晋文公闻之大喜,回国后赏功罚罪,对这次战役进行总结,然后以君子之言,赞扬晋文公的霸业。至此,叙述圆满结束。
《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如,作者在总结城濮之战经验时云:“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僖公二十八年)不仅是城濮之战,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而且叙述中往往还带有神秘因素。以《左传》中常出现的预兆为例,这些预兆大都有道德化倾向: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
这些预兆有时是智者的言论,有时则是占卜、梦境、天象等的神秘暗示。如“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在“僖公十年”就有已故晋太子“敝于韩”的预言;“僖公十四年”又有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的预言,战前又有秦卜徒父释卦之兆,晋惠公不从占卜之失。在这些看似神秘的预兆之后,是晋惠公违礼、失义、背信之举。作者面对既成的历史事实,根据历史人物的言行得失,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加入种种神秘化的传说故事,来预示事件的结局,解释事件的因果关系。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左传》是一部历史着作,但作者有时就像一个故事讲述者,把事件叙述得颇具戏剧性。大量生动的戏剧性情节,使这部作品充满故事性。不仅如此,《左传》有的叙事记言,明显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出于臆测或虚构。如“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介子推母子间的对话,不可能有第三者在旁听见或记录,当是作者根据传闻和揣想虚拟而成。这种写法,可以看作后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对话的萌芽。《左传》中还记述了大量的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如“成公十年”记晋景公之死,情节曲折怪诞,用三个梦构成了互为关连的情节。写晋侯所梦大厉,画鬼如生动的令人毛骨悚然;病入膏肓的描写,极为生动有趣;桑田巫释梦之语,小臣之梦的印证,更是充满神秘色彩,仿佛志怪小说。
人物是叙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左传》中描写了各种人物,但《左传》的写人还不像纪传体历史着作在一个专章中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没有像后世小说那样塑造人物形象。由于它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左传》中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如郑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郑子产、齐晏婴等等,都是通过数年行迹的积累来表现的。
《左传》中还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的仅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断,反映的是其性格中的某一方面。这些形象往往非常生动传神,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如“晋灵公不君”中,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武士(宣公二年),齐晋{安革}之战中代君就俘的逢丑父等(成公二年)。
《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左传》有些描写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晋文公是《左传》中着力歌颂的人物(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他由一个贵公子成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熟过程。楚灵王是《左传》中被否定的国君形象(襄公二十六年至昭公十三年),他在即位前的争强好胜,野心勃勃,弑王自立,即位后的残暴,骄奢狂妄等,都显示出他确实是个昏君。但同时,作者又表现了他宽容纳谏,知过能改,不记前怨,风趣等性格特点,并写了他最后悔恨自己的残暴,刻画出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
《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人物性格得以展现,形象得以完成。如成公二年的齐晋{安革}之战,《左传》这样描写战争场面,展现战争的全貌,表现人物个性:
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桴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却克受伤,解张、郑丘缓鼓励他坚持战斗,当时战场上紧张激烈的场面,可想而知。三人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气概,在对话和行动描写中,也得到充分表现。
《左传》在战争描写中还有许多与整个战局关系不大的事,这些事只是反映了战争的一些具体情状,在战争中并不具有重要意义。《左传》还在复杂的战争过程、政治事件中,大量描写细节。作为历史着作,这些描写内容完全可以不写或略写,但《左传》却大量地描写了这些琐事细节,它们在叙事生动和人物刻画方面具有文学意义,如“宣公二年”的宋郑大棘之战,其中狂狡倒戟出郑人,华元食士忘其御羊斟,华元逃归后与羊斟的对话,城者之讴等,都非这次战争的重要事件,但如果只写宋郑战于大棘,宋师败绩,郑人获华元,华元逃归,则必然使叙事枯燥无味,毫无文学性可言。
正是这些次要事件中的细节描写,才增加了叙事的生动传神。又如“宣公四年”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写了公子宋食指大动,郑灵公食大夫鼋不与公子宋,公子宋怒而染指于鼎等细节,整个事变由食无鼋这件小事引起,而公子宋的贪馋好怒,公子归生的迟疑懦弱、郑灵公的昏庸可笑都在生活细节的描写中表现了出来。再如“哀公十六年”记楚国白公之乱这一政治事件,最后写叶公子高平叛,没有着重写叶公的重大军政措施,而就叶公是否该戴头盔这一细节反复渲染:
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若见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犹将旌君以徇于国,而又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进。
突出国人对叶公的爱戴和叶公急于争取国人的心理。叶公平叛之所以成功,他的可贵之处,都在叶公免胄的细节中表现出来。
《左传》中的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他国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这类记言文字无不“文典而美”,“语博而奥”(刘知几《史通》卷十四《申左》),简洁精练,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如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的说辞,秦晋联合攻郑,烛之武作为郑使出说秦伯。他着重对秦、晋、郑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作了具体的分析。先把郑国之存亡放在一边:“郑既知亡矣。”再叙述郑亡并无利于秦:“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然后归结到保存郑国于秦有益无害:“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最后还补叙昔日晋对秦之忘恩负义以加强说服力。
说辞有意置郑国利害于不顾,而处处为秦国考虑,委婉而多姿,谨严而周密。因此,能打动秦穆公之心,使他不但退兵,还留秦将杞子等三人率军助郑守卫。晋人也只好退兵,郑国得以保全,充分显示了烛之武说辞的分量。《左传》中的行人辞令、大夫谏说佳作甚多,如隐公三年石碏谏宠州吁,隐公五年臧僖伯谏观鱼,桓公二年臧哀伯谏纳郜鼎,桓公六年梁谏追楚师,僖公五年宫之奇谏假道,僖公十五年阴饴甥对秦伯,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师,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子,成公十三年吕相绝秦,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坏晋馆垣,等等。
这些辞令,由于行人身份及对象的不同而风格各异,有的委婉谦恭,不卑不亢;有的词锋犀利,刚柔相济。这些辞令又因事因人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个性特点,但都用辞典雅,渊懿美茂,生气勃勃。《左传》的辞令之美,“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史通》卷十四《申左》)大约当时的外交辞令已很讲究,史家记述时又加修饰,故而文采斐然。
《左传》叙述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如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中,写晋师溃败时的狼狈之状云:“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为争渡船逃命,先上船者以乱刀砍争攀船舷者手,落入船中的手指竟然“可掬”。简练的一句话,写尽晋师争先恐后、仓皇逃命的紧张混乱场面。同年冬天,楚国出师灭萧,将士“多寒”,于是“(楚)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楚王劳军的体恤之语,温暖将士之心就如披上了绵衣。以一个贴切的比喻,形象生动地写出了楚王慰勉之殷,将士愉悦之情。“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史通·叙事》)
国语
关键名词:成书及体制、记言为主记事为辅
《国语》是一部国别史,全书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成书约在战国初年。各国“语”在全书所占比例不一,每一国记述事迹各有侧重。《周语》对东西周的历史都有记录,侧重论政记言。《鲁语》记春秋时期鲁国之事,但不是完整的鲁国历史,很少记录重大历史事件,主要是针对一些小故事发议论。《齐语》记齐桓公称霸之事,主要记管促和桓公的论政之语。《晋语》篇幅最长,共有九卷,对晋国历史记录较为全面、具体,叙事成分较多,特别侧重于记述晋文公的事迹。《郑语》则主要记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楚语》主要记楚灵王、昭王时期的事迹,也较少记重要历史事件。《吴语》独记夫差伐越和吴之灭亡,《越语》则仅记勾践灭吴之事。
《国语》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西周以来的敬天保民思想在书中得到了继承。虽然《国语》许多地方都强调天命,遇事求神问卜,但在神与人的关系上,已是人神并重,由对天命的崇拜,转向对人事的重视。因而重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以民心的向背为施政的依据。如《鲁语上》鲁太史里革评晋人弑其君厉公时,认为暴君之被逐被杀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臣民的反抗行为无可厚非。又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中,邵公主张治民应“宣之使言”,从人民的言论中考察国家的兴衰,政治的得失,国君只有体察民情,行民之所善,去民之所恶,增加人民的财富衣食,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国语》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国语》记言文字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生动活泼而富于形象性。当然,由于《国语》是各国史料的汇编,素材来源不一,编者亦未作统一润色,其记言水平参差不一,风格也颇有差异。比如《周语》旨在说教,行文委婉,多长篇大论,《鲁语》篇幅不长,语言隽永,《楚语》、《吴语》、《越语》则文字流畅整饰,颇有气势。《国语》中的应对辞令,有的与《左传》相同,但文字不如《左传》精彩,有的则难分高下。有的为《左传》所不载的辞令也颇有特色。如周襄王不许晋文公请遂,辞婉义严(《周语中》),越王勾践求成于吴,辞卑气低等(《吴语》),都是很有特色的辞令。而《国语》中一些议论说理文字,往往也精辟严密,层次井然。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鲁语下》敬姜论劳逸,《晋语八》叔向贺贫,《楚语下》王孙圉论宝,都历来为人们所称道。
《国语》虽然记言多于记事,但《国语》没有单纯的议论文或语录,有一系列大小故事穿插其中,因此表现出叙事技巧和情节构思上的特点,有时也能写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总的说来,《国语》也有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但不及《左传》普遍、完整。《国语》中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及经过都是一笔带过,而把重点放在大段的议论文字上。但《国语》也有情节生动曲折,极富戏剧性的叙事,如《晋语》前四卷写晋献公诸子争位的故事,献公宠妃骊姬的阴谋,太子申生的被谗冤死,公子重耳的流亡等,都写得波澜起伏,精彩纷呈。
其中有虚拟的情节,如骊姬夜半而泣(《晋语一》),谗太子申生,骊姬夜泣及其谗言,非第三者能知,显然是作者援情度理的虚构,刻画出一个口蜜腹剑,阴险狠毒的人物形象。其中也有精彩的描写,如为分化朝中大臣,骊姬宠幸的优施与朝中重臣里克饮酒,以歌舞暗示里克,将杀太子申生立骊姬子奚齐,里克夜半召优施,欲中立以自保等(《晋语二》),描写细致入微,具体生动,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点。
更有一些滑稽的小插曲,写得生动活泼,如重耳流亡到齐国后,安于寄人篱下的生活,其妻姜氏及从亡之臣子犯将其灌醉载之而行(《晋语四》),《左传》只写到重耳桓,“以戈逐子犯”,《国语》中还写了重耳子犯相骂的对话,幽默有趣,写出了重耳流亡集团的内部冲突。对晋献公诸子争位的叙述,展示了春秋时期一场复杂政治斗争的生动画卷,描绘出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国语》叙事的成就。
由于国别史的特点,《国语》有时的记叙某一国事件时,集中在一定篇幅写某个人的言行,如《晋语三》写惠公、《晋语四》专写晋文公、《晋语七》专记悼公事,《吴语》主要写夫差、《越语上》主要写勾践等等。这种集中篇幅写一人的方式,有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势。但尚未把一个人的事迹有机结合为一篇完整的传记,而仅仅是材料的汇集,是一组各自独立的小故事的组合,而不是独立的人物传记。总之,由于《国语》以记言为主,虽然叙事和刻画人物有一定特色,但文学成就比《左传》还是稍逊一筹。
战国策
《战国策》凡三十三卷,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时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主要记载了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其中文章不是一人所作,作者大多是战国后期纵横家,也可能有若干篇章是秦汉间人所作。最后由西汉刘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
与《春秋》、《左传》、《国语》主要反映儒家思想不同,《战国策》表现了纵横家思想,反映了纵横家的人生观。在政治上他们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肯定举贤任能,在生观上则是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不过,《战国策》的思想内容又比较复杂,所记人物也反映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既有讲权术谋诈,图个人功名利禄的朝秦暮楚之徒,也有“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之士(《赵策三》)。《战国策》的思想价值,在于它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士贵耳,王者不贵”(《齐策四》)的声音,反映出士人精神的张扬。书中大量描写策士奔走于诸侯之间,纵横捭阖,令“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刘向《战国策叙录》)的重要作用和社会地位,可以说是一部士阶层,尤其是策士行迹的生动写照。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书对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鲜明生动的描写,尤其是一系列“士”的形象,更是写得栩栩如生,光彩照人。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勇毅之士如聂政、荆轲、高节之士如鲁促连、颜斶等等,都个性鲜明,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代表了士的不同类型。由于作者对这些人物心仪不已,颇为倾慕,甚至不惜脱离史实,以虚构和想象进行文学性描写。《战国策》中,不是史实,出于虚构依托的内容颇多。如书中用力极深,描写得极成功的人物苏秦,其事迹言论有不少就是虚构的。至于在具体描写中,虚构的手法更为普遍,也更进一步。如《秦策一》写苏秦夜读,引锥自刺及慨叹之语,夜室独语,有谁知道,显然是作者根据传闻虚拟而成。而《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写邹忌看见徐公时“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不仅表现了邹忌内心的活动,而且涉及心理活动的过程,接近人物的心理描写,显系出于作者的想象。夸张虚构不合史着的要求,但却使叙事更加生动完整,更有利于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
《战国策》还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作者不满足于平铺直叙,有意追求行文的奇特惊人,如《燕策三》记燕太子使荆轲刺秦王,其中田光自刎以明不言,樊于期自刎献头以图报仇,易水送别,秦廷献图行刺等情节,出人意表,慷慨悲壮,于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人物性格得以生动展现。人物个性化的言行在《战国策》中很突出,如《秦策一》中,苏秦落魄而归后的刺股和喟叹,荣归故里时的感慨,其家人前倨后恭的言行等,都反映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而对苏秦归来时“羸縢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黧)黑,状有归(愧)色”的外貌神情描写,绵密细致,极为传神。
《战国策》在写人上,一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如《齐策四》冯谖客孟尝君,写冯谖弹铗而歌,焚券市义、营造三窟的事迹,冯谖一生的主要事迹尽在一篇中,人物形象和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类作品,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
《战国策》的“文辞之胜”,在语言艺术上的空前成功,是其文学成就的重要方面。其中策士廷说诸侯之辞,臣讽君主之辞,以及不同意见的辩难,都反映出春秋时期从容不迫的行人辞令,已演化为议论纵横的游说之辞。其文章艺术风格,前人概括为“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可说是《战国策》说辞的主要特色。
战国时代,君德浅薄,多庸主暴君,游士为说服君相,说辞大都不以直接方式,往往引类譬喻,借动物、植物或人们生活中习见的其他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达到辩说的目的。《楚策四》载庄辛说楚襄王,庄辛针对楚襄王淫逸侈靡、不顾国政而进谏,说明国君如此行径必遭杀身之祸。他运用四种譬喻,即蜻蜓为五尺之童所黏捕,黄雀被王孙公子射杀,黄鹄被射者用网罗捕获,蔡灵侯因放荡逸乐被楚大夫发用绳索捆缚。四种譬喻,由小到大,逐渐过渡到楚顷襄王本身,指出其所作所为,正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形象生动,引喻谐调,气势充沛,说理充分。再如《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也是从切身体验的生活趣事,来形象喻示所要阐述的道理,贴切深刻,饶有风趣,很有说服力。
《战国策》还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来增强辩辞的说服力。寓言的巧妙运用,成为《战国策》文章的一大特点。如《燕策二》苏代以鹬蚌相争,说赵惠王不应伐燕,以免强秦坐收其利。这类例子《战国策》中俯拾皆是,如“画蛇添足”(《齐策二》)、“狐假虎威”(《楚策一》)、“南辕北辙”(《魏策四》)等等。这些寓言大都即事编撰,独出心裁,比附现实,以表情达意。用具体的形象概括抽象的道理,表现出极强的艺术力量。
《战国策》的铺张扬厉,气势充沛,还与行文的夸张铺陈,大量运用对偶排比有关,如《赵策三》“鲁仲连义不帝秦”,列举了周烈王之斥齐威王,殷纣王之醢鬼侯、脯鄂侯、拘文王,齐闵王之欲仆妾邹鲁等,肆意夸张铺隐,极言尊秦之害。又如《齐策一》记苏秦说齐王合纵,极力夸张渲染齐国之强,临淄之胜,排比对偶层出不穷,文辞瑰丽多姿。
与其游说之辞一样,《战国策》的叙述语言,也长于铺张渲染。“苏秦始将连横”(《秦策一》)写苏秦说秦王不行时的狼狈之状,发迹后路过家乡时的踌躇满志,“荆轲刺秦王”(《燕策三》)写荆轲易水送别时的慷慨悲壮,都是典型的例子。《战国策》叙述语言有时描写相当精细。苏秦刺股(《秦策一》),触龙入朝(《赵策四》),邹忌窥镜(《齐策一》)等,写的都是琐屑细节,却展现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尤其是荆轲刺秦王的场面,描写人物动作神情,极为细致传神,荆轲的豪迈暇豫,秦王的惊慌失措,殿上殿下的混乱惊扰,这些顷刻间发生的惊险紧急场面,作者一一道来,清晰详尽,有条不紊,如同电影镜头,作者对叙述语言运用之娴熟,令人惊叹。
《战国策》文章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瞻的文采,是当时纵横捭阖时代特征的体现,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水平。
影响
《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的叙事传统和语言艺术对史传文学、散文和小说创作的滋养,尤为明显。
先秦叙事散文的体例、思想、写作艺术等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有直接启发。《史记》体例是在先秦编年史、国别史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而《汉纪》、《资治通鉴》等,则是《春秋》、《左传》编年体史书的直接继承。先秦叙事散文记述历史事件时直书其事、褒贬鲜明的特点,《左传》、《战国策》高超的写作艺术,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史传文学着作《史记》就吸收了《左传》、《战国策》的写作技巧,对其中的一些史实略加改动便加以运用。少数特别精彩的篇目,甚至不加改动就直接录入。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继承了《左传》开创的既叙述故事,又描写人物的形象生动的写史传统,他们不仅是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文学家,其作品既是历史着作,又是文学作品。《左传》的叙事艺术,如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发展过程的重视,对历史事件故事化的描写,历史事件的叙述条理井然而又富于变化等等特点,在后代史传文学中都有充分体现。《左传》简练蕴借的语言风格,为后代史家所继承,而《史记》的奇谲文风,显然与《战国策》的辩丽恣肆有直接的关系。总之,先秦叙事散文是我国史传文学最初成就,其沾溉于后世,不言而喻。
先秦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成为后世散文写作的楷模。秦汉以后,《左传》的文章一直为人们所喜爱,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古文家,都非常推崇《左传》,并把它作为学习对象。韩愈《进学解》说他“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古代作品中,就包括《左传》。宋人把《左传》与《史记》、韩文、杜诗相提并论,同作为文学范本。情韵丰富的《左传》散文,也深为清代桐城派散文家所推崇。
对《国语》语言艺术的赞誉,历来甚多。柳宗元尽管曾作《非国语》批评《国语》的某些思想,但在其“序”中还是认为“其文深闳杰异”,其为文即以《国语》为法。汉初散文,尚有战国遗风,贾谊,邹阳等西汉前期散文家的作品中,更是可以明显看出《战国策》文风的余绪。这种影响持续不断,在苏洵、苏轼等后代作家的散文中,还可以体味到先秦叙事散文的神韵。《战国策》的文章,对汉赋的产生也起过促进作用。汉赋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扬厉的风格,都可以看出对《战国策》的借鉴。
先秦叙事散文的叙事艺术,对我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独特的艺术个性的形成,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首先,先秦叙事散文叙述历史事件中表现出的褒贬分明的倾向性,对我国古代小说注重教化作用有直接的影响,并且,《左传》、《国语》等作品中用“君子曰”等对事件进行的评述,在文言小说如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书中被直接借鉴,就是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有明显的痕迹。其次,先秦叙事散文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
我国古代小说常按时间顺序安排结构,串联情节,特别重视对故事起因、过程、结果的完整描写,并以倒叙、插叙、补叙等方式追叙事件的起因,以预叙的方式暗示故事的结局。这些都是《左传》等散文中就已形成的叙事传统。第三,我国古代小说写人的基本手法在先秦叙事散文中已初具规模。我国古代小说主要通过描写人物个性化的言行,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表现人物性格,而较少长篇的外貌描写、心理描写,而这正是《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写人的共同特点。
第四,我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作品对历史题材的重视,也是受先秦叙事散文的启示。这不仅是指诸如《东周列国志》之类以先秦叙事散文为题材的作品,同时,古代小说大量采用历史题材,也和我国叙事文学最初成果是产生在历史着述中不无关系。
研究机遇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和《清华简》相继面世,一大批不为人知的先秦散文重见天日。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新的文献学术资料面世,都会带来一场文化学术思想的深刻变革。世纪之交的出土文献都集中在先秦,而且是以散文文献为主,这使先秦散文史研究迎来重大学术机遇。
发展简史
此前文学史家讲先秦散文发展史,大都把先秦散文分为“先秦历史散文”和“先秦诸子散文”两大部分,认为这两个部分各有各的发展线索,彼此互不相干。讲“先秦历史散文”,论者是从甲骨文、金文、《尚书》、《春秋》讲到《左传》《国语》《战国策》;而对“先秦诸子散文”,则将其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论语》《老子》《墨子》为第一阶段,《孟子》《庄子》为第二阶段,《荀子》《韩非子》为第三阶段。这个知识体系写在大学教科书里,传授给一届又一届学生。如今,出土竹书对这个先秦散文史理论框架形成了有力的冲击。
据考古专家研究,“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入墓年代,大约在战国中期偏晚,出土竹书应该是在此之前的孔门七十子后学作品。“上博简”儒家竹书可能多出于孔门七十子之手,“郭店简”儒家竹书要稍晚一些,应该是七十子后学之作,有人说它们是子思学派的作品。
历史审视
将出土竹书与传世文献进行比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它可以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某些传世文献的作者和写作年代。传世文献中有一批记载孔子应对弟子时人的作品,与出土竹书《民之父母》《子羔》《中弓》《孔子见季桓子》《季庚子问于孔子》等在内容和形式上相近,如《礼记》中的《檀弓》《哀公问》《曾子问》《礼运》《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儒行》,《大戴礼记》中的《主言》《五帝德》《子张问入官》《卫将军文子》《哀公问五义》《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闲》,以及《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曾子制言中》《曾子制言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圆》等。
若遵出土竹书之例,大小戴《礼记》这些文章应该作于春秋战国之际孔门七十子后学之手。与“郭店简”中的《缁衣》语录体形式相近的还有《礼记》中的《表记》《坊记》和《中庸》。《隋书·音乐志》引沈约之说,以为《中庸》《表记》《坊记》《缁衣》四篇皆取自《子思子》。同样,大小戴《礼记》中还有一批与上博简《内礼》相似的记载礼仪的作品,如《礼记》中的《曲礼》《文王世子》《礼器》《郊特牲》《内则》《玉藻》《明堂位》《丧服小记》《大传》《少仪》《杂记》《丧大记》《祭法》《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深衣》《投壶》,《大戴礼记》中的《武王践阼》《盛德》《明堂》《诸侯迁庙》等,这些礼学文献应该是孔子所述七十子后学所记。
此前不少学者把大小戴《礼记》看作是秦汉文章,出土竹书表明,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大小戴《礼记》中确有若干秦汉文章,如《月令》《礼察》《保傅》等,但只占极少数,这两部文集中绝大多数文章应该作于春秋战国之际和战国前期,它们是孔门七十子后学的作品。结合出土竹书与传世文献来看,七十子后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说理散文流派,这个流派包括七十子和他们的弟子后学,可以将他们合称为七十子后学①,他们人数多达数百人,所写的文章远不止一部《论语》,大小戴《礼记》中绝大多数文章、《孝经》、《仪礼》、郭店简以及上博简中的儒家文献,都是他们的散文作品。
《汉书·艺文志》着录的七十子后学散文有二百多篇②,今天所能见到的大约有一百多篇。我们可以将这些散文统称为“七十子后学散文”。在七十子后学散文中,目前只有《论语》被写进中国文学史,这对七十子后学是不公平的,其实只要我们不带偏见,就应该承认,除那些记载礼仪的作品外,“七十子后学散文”大都具有文学价值。
出土竹书的面世,不仅为孔门七十子后学夺回了一大批作品着作权,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我们以全新的学术目光来审视先秦散文发展史。出土竹书中有一批记载孔子应对弟子时人的对话体散文,如《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中弓》《孔子见季桓子》《颜渊问于孔子》《史蒥问于夫子》《鲁穆公问子思》等,它们与《论语》、《孝经》、大小戴《礼记》等记载孔子言论的传世文献一样,都是当年孔门七十子后学记下的。这种对话体散文形式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孔子师徒之前就早已存在,它发轫于《尚书》,成熟于《国语》。
《尚书》中的《西伯戡黎》《微子》《洪范》《洛诰》《顾命》等,都是商周时期的对话体散文。《国语》继《尚书》之后发展了对话体,形成了主客问答的形式格局,问句提出问题,而答语是文章的主要部分。这些商周对话体散文有一个叙事框架,不少人误以为它们是叙事散文,从而将它们归于“先秦历史散文”,而把它们与“先秦诸子散文”割裂开来。其实,商周对话体散文兼有叙事、说理的因素,而其主体是记载人物言论,这些言论有论点,有论据,应该视为说理散文。
七十子后学的对话体散文与《尚书》《国语》对话体散文不是偶然的形式相似,而是七十子后学对前人的刻意传承,他们效法商周史官,采用商周记言散文形式,执笔记载孔子言行。七十子后学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有所创新,这就是去掉此前史官记言散文的叙事框架,使之成为纯粹的说理散文。像《大戴礼记》收录的曾参名下十一篇文章,就是比较成熟的专题论文,我们可以说,中国纯粹的说理散文成型于七十子后学之手。七十子后学的语录体散文,也可以从《尚书》文诰中找到源头,像《盘庚》《高宗肜日》《大诰》《康诰》等,都是王侯政治言论的记录,只不过它们是以国家意志的面目出现而已。
七十子后学所记载的孔子语录,在内容上由务实变为务虚,由政治变为伦理道德,文化学术意味明显增强。从七十子后学散文往下看,战国诸子散文虽然堪称百花齐放,在散文篇幅、风格、技巧、手法、逻辑结构等方面较七十子后学散文有很大发展,但从文体上看,要之不出对话体、语录体、专题论文几大文体,而这几大文体在七十子后学散文中均已基本成熟。我们完全可以说,战国诸子百家散文是沿着七十子后学的路子走下来的。将商周对话体散文、七十子后学散文与战国诸子百家散文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其中的传承与发展。以前由于七十子后学散文这个中枢环节被人为遮蔽,导致人们看不清先秦散文发展演变的真实脉络,所幸的是“郭店简”“上博简”等竹书相继出土,我们才能拨开重重迷雾,还原先秦散文发展的真正历史面目。
一部先秦散文的发展史,从先秦历史散文到先秦诸子散文,并不是彼此互不相干,它们的内脉其实是相通的。只是从先秦历史散文到先秦诸子散文,其间有一个枢纽,这个枢纽就是七十子后学散文。七十子后学散文是先秦散文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处于上承历史记言散文、下启战国诸子百家说理文的中枢地位。这是出土竹书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出土文献呼唤新的先秦散文史。
道教散文
从形式上看,道教散文主要包括三类:议论散文、叙事散文、赋体散文。道教议论散文是阐述道教教理的一种文学体裁。在早期,道教议论散文主要是语录体散文,这种散文采取了“天师”与“真人”等神仙人物问答的方式来表达道教关于自然、社会、人生的看法。例如《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大体上属于这种形式的散文。试看该书乙部的一段对话:“真人问神人:‘吾生不知可谓何等而常喜乎?’神人言:‘子犹观昔者博大真人邪?所以先生而后老者,以其废邪?人而独好真道,真道常保而邪者消。凡人尽困穷,而我独长存,即是常喜也。’”
这种对话不同于小说中的人物对话,语录文作者的目的并不在表现人物个性,而只是借神仙人物之口来论述教理。所以其行文一般是问话短,而答语长,旨在说理。这种作品当是适应早期道教师徒共探教理的需要而产生的。当然,《太平清领书》中的语录体散文还有一些是通过辑录古书而来的。该书卷四十一谈及道派首领发动有一定文化水准的道教信徒拘校古书之事。同时,他们还注意记录群众中的“善辞诀”、“人情辞”,作为“洞极天地阴阳之经”。
这种通过摘录编辑而成的文章也属语录文。其特点是语言比较质朴,就当时来说,算是比较口语化的。例如《太平经》卷四十七《上善臣子弟子为君父得仙方诀》就使用了不少“噫”、“唯唯”之类流行口语,增加了对话的气氛。与此相联系的是类比手法的广为应用。为了深入浅出地阐述教理,早期道教领袖注意通过类比以说明问题。从类型上看,有具体类比与抽象类比;从对象上看,有物比人、有人比物等等。像《太平经》卷四十五《起土出书诀》将地皮比人皮,以地下出水比人皮出血,认为人皮虽有薄有厚,但不能因为皮薄把他刺出血来就无罪;同理,地皮也有薄有厚,乱挖一通,不惜遗力想见其水,其过与伤人见血不异。
这种类比虽然浅近,但对于阐明保护生态平衡观点来说则有一定说服力。《太平经》的这种语录体散文对后代的道教经典创作影响颇大。魏晋以后,以“语录”为名的道教典籍层出不穷。诸如《灵宫法语》《晋真人语录》《丹阳真人语录》《无为清静长生真人至真语录》《盘山栖云王真人语录》《清庵莹蟾子语录》《三十代天师虚静真君语录》《虚静冲和先生徐神翁语录》《真仙真指语录》等等。这些名为“语录”的典籍虽然也包含一些诗歌作品在内,但基本上则属语录体散文。当然,语录体散文也有其局限性,它没有较严密的体系,结构也较为松散。